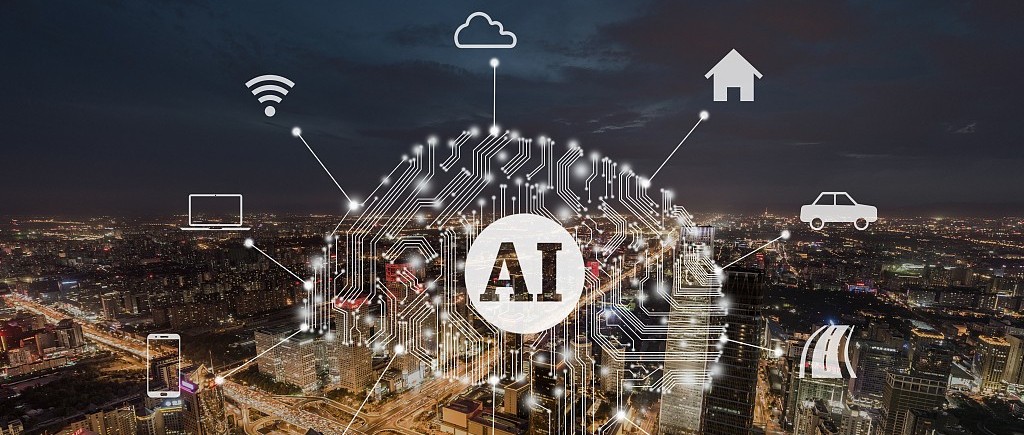我的童年是在辽宁西部小城度过的,在那里,我结识了一群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亲如姐妹,相伴60余年。从我们父母一辈就相识,是认识一辈子的老同事、老邻居,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家属大院里长大,从4-5岁的孩童,到上学,上山下乡,进城工作,结婚生子,直到年老退休。我和这群姐妹相伴了大半辈子,是彼此生命历程的见证者和分享者。
小伙伴初见:儿时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
那是五十年代末,1959年,我和同一个大院儿的小姐妹,先后跟随各自的父母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名次扩展请见文末),来到凌源这个辽宁西部的小县城。
记得绝大多数家庭都是鞍山搬迁来的,只有我家是从丹东凤城搬迁来的。我们被分配到矿山平房家属院,都住在前后栋房。我家和韩家,周家住同一栋平房,那时我们还都是天真无邪的孩子呢,听父母说刚搬来时,新盖的房子还没有完全干透就搬进去了。
记得燕子姐最大才六岁,我和慧儿五岁,雅丽和琴儿刚四岁,小不点娟子只有三岁,韩大爷家大姐和三位哥哥稍大些。
我们小时候,家里条件都不太好,玩的玩具也都是不花钱或者独创的。
穿的也很简朴,鞋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冬天能穿上棉衣,夏天能换上单衣就已经不错了,很少有换洗的衣裤。夏天一般都是洗好晾干就穿,冬天贴身根本没有衬衣衬裤穿,只有背心和短裤,棉衣棉裤能有外罩套就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了。
吃的是国家供应粮,孩子大点都不够吃,细粮很少,多数是苞米面,高粱米。虽然很苦,但我们却觉得很快乐。
妈妈和韩娘的关系最好,她们相差11岁。韩娘是称职的大姐,还是业余助生婆呢。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都主动帮忙,听妈妈说,她经常起早去粮站排队买粮,还给韩娘占位置呢。
爸爸挣了很多年59元工资。那个年代谁家先开工资就先去谁家借用,少则五元,多则十元,如果数额较大,就去平时关系处的比较好的双职工人家借用,等自己家发工资了再还回去。
儿时难忘的趣事
我和我的小伙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我们无忧无虑,经常一起玩各种自创游戏,跳格子,跳皮筋,踢键子,玩羊嘎拉(一种北方游戏)攻碉堡,用手勺杏核,黑天就捉迷藏,还经常去韩大爷家玩跳棋。
雅丽经常不服输,跳棋玩得大有长进,更忘不了慧妹小时不知为什么经常哭,谁惹她也哭,看她一眼她也哭。
我和雅丽经常吵嘴架玩,常说:“你家好,木头凳。”,我也说:“你家好,红草沟。”
其实“木头凳,红草沟”都是老家地名,真是太有意思了!
还记得小时候,我在路旁啃榆树皮,大功将要告成的关键时刻,那边小孩交战打起来了,拿石头撇来撇去,没留神,一块石头把我的前额打破了,鲜血顺着小脸往下淌,我吓哭了,然后就有小伙伴跑回家告诉了我妈。
妈妈把我领到卫生所包扎好就回家了,我挂了彩,妈妈过后批评了我,多危险啊!如果打在眼睛上那可就糟糕了,好几十年了现在还有留下的小疤痕呢。
记忆中的往事太多,数也数不清。让燕子姐至今念念不忘的是,有一次韩娘给几个女儿留的三张油饼拴在窗户上,不知哪个小馋猫给偷吃了,小不点娟子忍不住就哭了起来。二个姐姐告诉娟妹别说出去,但娟妹还是无意中说漏了嘴。
妈妈留她们姐仨在我家吃的中午饭,多加了一瓢水,粥变稀了,但我们几个吃的都挺乐呵,最起码小肚子不会咕咕响了。
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耍,那时家里都缺钱,布票是统一发放,谁家都有点短缺。韩家大姐心灵手巧,经常给几个妹妹用手绢设计背心,当时可让我们羡慕了。
大姐歌还唱得好,经常从她家传出那动听的歌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也许韩家真的有遗传基因,韩娘歌唱得就好,她们家七个儿女,各个唱的棒,都能开场音乐会了。
家有少女初成长
悠悠岁月,转眼我们都上学了,每天早晨经常三人一群五人一伙一起去学校,晚放学又一起回家。燕子姐想法最多,跳棋也玩得最好,她为了逃避干活,每次快吃饭,吃完就快跑,谁喊她也不回头!
雅丽不太爱说话,有个可爱的小虎牙,但闷起来,十条牛都拉不动。
琴儿慢声慢语,陌生人前话更少,我们相处久了,却感觉她和蔼可亲,略有点倔。她还有个乳名,叫[huangbangzi],那个年代,家里经常起个听起来好养活的乳名。听说这个名字是她妈妈给起的娇名。 我们都很喜欢和她玩。
她家叔婶也特别好,还收养了烈士哥哥的三岁遗孤儿子,把亲侄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但在称呼上始终没有改变,他们说这样叫好养活。
萍儿最爱生气,经常莫名其妙就来点气,谁哪句话说的不对心思也来气。韩大姐的儿子立新刚学会说话,吐字还不清,Qin晓萍经常被他读成[Qixiaoqing],我们听起来就是气晓萍,小时候我们因为一句谐音,就欢乐得不得了。
我比较憨厚,谁跟不跟我玩,理不理我,都没有关系,和谁都可以玩在一起。
萍儿是我们几个最累的,经常后背一个妹,手领一个弟,有时家里一边煮着高粱米粥,一边跳格,每隔一会回家看看,如果做糊了,那可惨了,挨妈妈训是轻的,重的惩罚要挨揍。
萍儿,和青儿家姊妹多,进了秋天就开始捡煤糊,拿着小铁扒经常弄成小花脸。冬天手都冻红了,煤葫都能堆成一座小山了,冬天取暖几乎不用买煤了。
难忘姐妹情,相伴一辈子
走过春夏秋冬,岁月的列车把我们从童年,少年,青年,直奔中年,又载入老年。如今,我们真的慢慢变老了,头发也变白了许多,脸上不知不觉长了很多皱纹,但童年的无忧时光常常让我们想起儿时的歌谣:
挤进城,跑马城,
马城开,打个小姐送信来,
你要谁?
我要【xxx某人名字】
儿时那些简单却带给我们无限欢乐的游戏,至今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想起小时候的时光,就想印在梦里,想起来在梦里也会笑醒。
光阴似箭,转眼我们小姐妹大部分都升级做姥姥了,在世的老辈已经不多了。雅丽还有年近九十岁的老爸,华儿有90多岁老妈,青儿有80多岁老妈,就属萍儿最幸福,还有父母的陪伴,父亲94岁,母亲85岁。
珍惜今天的拥有,无论何时少留遗憾,是最重要的!我们其余几个姐妹都已失去双亲,真羡慕有父母陪伴的幸福时光。
说起韩家五哥那可是我们这辈人的楷模,他常说;父母能养我们小,我们一定要养父母老啊!
韩娘患脑溢血后遗症几年,一直住在他家,直到韩娘95岁去世。做为一个男人,整天囚在家里,真不容易!
韩娘在世时,五哥和姊妹不攀不比,常年陪伴老母,觉都睡不好,但他却没有任何怨言。燕子姐为了减轻哥嫂的负担,经常去帮助洗涮,其他人也都常去看望。
五哥已经近70了,他常说:“对待老人就应该像对待老小孩一样呵护,不但要做到孝,而且还要做到顺。这是我们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
光阴似箭,转眼我们都已不再年轻,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但我们的感情从没因时间而改变,我们之间那份情,无人能代替,早已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偶尔聚在一起经常聊到深夜,总有说不完的话,常常忘了时间。
人前我们有彼此才懂得暗语、笑话 ,人后我们有彼此之间的故事和情感,有彼此才能开的玩笑。
好久没联络了,并不是距离远了,好久没有消息了,并不是关心没了。从成为朋友那一刻起,你我就不曾远离,就注定扎根在我们心里。
现在,我和雅丽在外地帮助子女照顾孩子。每次回家乡,我们都会一起小聚,聊分别后的思念。那种在彼此面前才有的无拘无束和发自心里的笑,让我们特别珍惜这份从小到大的情谊。
2016年2月25日,我在微信建立了童年的回忆群,给姐妹们创造了一起交流互动的平台。那些最美好的童年时光,伴随我们走过了60年,因为在乎,从未忘记。
2019年,腊月二十八,我们最好的闺蜜淑琴因多年肾功能减退,最后导致肾衰竭综合症,突发心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和燕姐、雅丽,代表萍儿专程送她最后一程。
很遗憾2018年夏天,我回家乡几个姐妹想去看望淑琴,她说啥也不让去。也许,她不想让我们看到她生病时的模样。淑琴,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姐妹,是我们记忆中最美好、亲切的模样。
回想我们几十年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当情不自禁看到我们在一起的合照留念,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难受。泪水夺眶而出。她刚刚63岁,就这样悄悄的走了……
走的那么匆忙,留给亲人和朋友是永远的怀念。再也没有机会相见,想起每次小聚,无论是盛夏还是寒冬她都第一个坐车过来。那种姐妹情让我们难舍难分。更是我们童年伙伴一生的回忆。
多想能留住你
多想牵着你的手
多想能再见你
想你只能在梦里
留在我们记忆里
天堂没有苦难
愿你喜乐安康
来生约好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