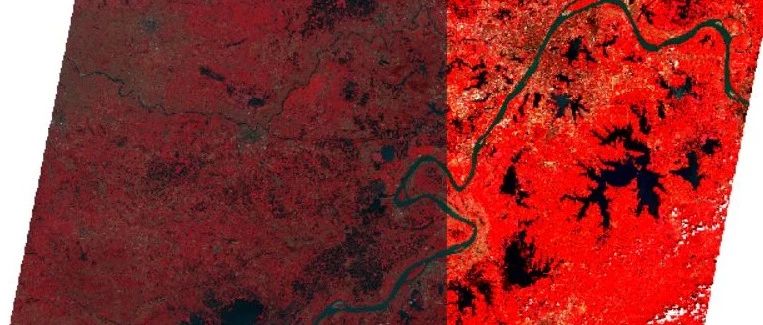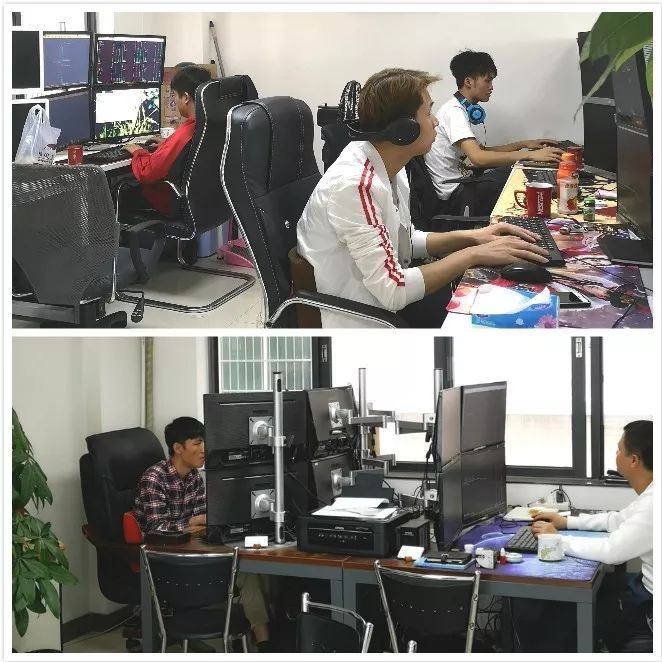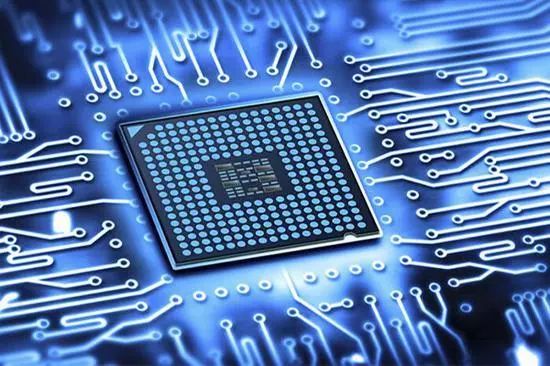在刚刚结束的戛纳电影节上,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获得最高大奖金棕榈。赢得一片好评的韩国导演李沧东作品、改编自村上春树小说的《燃烧》只获得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特别被请出的戈达尔,被授予了特别金棕榈奖。
女星艾莎·阿基多在颁发影后奖项时,当场表示1997年、21岁的她在戛纳电影节被哈维·韦恩斯坦强奸,“这个电影节就是他的捕猎场”。
下面送上完整的获奖名单。
【主竞赛单元】
金棕榈最佳影片:是枝裕和《小偷家族》
评委会大奖:斯派克·李《黑色党徒》
最佳导演:保罗·帕夫利科夫斯基《冷战》
最佳男演员:马尔切洛·丰特《犬舍惊魂》
最佳女演员: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 《小家伙》
最佳剧本:爱丽丝·洛尔瓦彻《幸福的拉扎罗》、贾法·帕纳西《三张面孔》
评审团奖:纳迪·拉巴基《迦百农》
特别金棕榈奖:让-吕克·戈达尔《影像之书》
短片金棕榈:查尔斯·威廉姆斯《芸芸众生》
短片特别提及奖:魏书钧《延边少年》
酷儿金棕榈:卢卡斯·德霍特《女孩》
金摄影机最佳长片处女奖:卢卡斯·德霍特《女孩》
【一种关注单元】
最佳影片:阿里·阿巴西《边境》
评审团奖:若昂·萨拉维扎、Renée Nader Messora《死人和其他人》
最佳导演奖:谢尔盖·洛兹尼查《顿巴斯》
最佳编剧奖:Meryem Benm'Barek-Aloïsi《索菲亚》
最佳演员:维克多·博斯特《女孩》
【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
主竞赛单元:李沧东《燃烧》
一种关注单元:卢卡斯·德霍特《女孩》
平行单元:Zsófia Szilágyi《一天》
《小偷家族》
是枝裕和的新片《小偷家族》讲述一个旧住宅区里,打散工的父亲和儿子,合作盗窃。有一次回家的路上,在寒冷的街上发现一个可怜的女孩,就把她带回家了。妻子很生气,但还是照顾起这个女孩……一家人都靠着祖母的退休金生活,贫困而幸福,但事情有了变化……
这是是枝裕和擅长的家庭题材,又回到了他早期介入社会现实的硬度。这也是日本时隔21年后再次获得金棕榈大奖。
荣获过金棕榈的日本影片:1953,衣笠贞之助《地狱门》;1980,黑泽明《影子武士》;1983,今村昌平《楢山节考》;1997,今村昌平《鳗鱼》;2018,是枝裕和《小偷家族》
《小偷家族》的很多地方让人想起《无人知晓》
是枝裕和被西方影评界视为“新日本电影新浪潮”一代“思想最为严肃的导演”。但他在日本并没有像在国际上那么受欢迎。
是枝裕和最喜欢的导演是侯孝贤,《童年往事》曾经狠狠地激起他的乡愁,让他开始感受祖辈和父辈的人生。他的祖父与祖母都姓是枝,在当时的日本,同姓不可通婚,两人便私奔到了台湾,是枝裕和的父亲便是在高雄出生的。”二战”之后,父亲被遣返日本。生长于上世纪60年代东京的是枝裕和常常不甚着意地听父亲讲述自己年轻时代的往事、那一代人的理想和命运、战争与历史带给人的惊愕和茫然。直到他在侯孝贤的电影里看到台湾,父亲口中带着晦明而温柔的光晕的台南,以及那逝去的时光,像一首古老的歌曲,一下子被唤了起来。他的眼睛里带上了一抹前尘旧梦,看什么都习惯于隔开一定距离、居于幽暗而独自体味。
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是枝裕和进入TV Man Union(电视人联合会),拍了将近十年的纪录片。
他的纪录片涉及的主题十分广泛。既有社会事件,如伊南小镇学校一个班级的学生喂养一头小牛的经过,社会福利局官员由于理想幻灭而自戕的事件后续;也包括诗人宫泽贤治、电影导演侯孝贤和杨德昌,以及流行乐手Cocco等人的传略;他还关注一些社会边缘人,如战时流落日本并冒充日本人50年之久的朝鲜人,日本首位公开承认自己经由同性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的平田裕,由于一起医疗事故而导致短期记忆丧失的关根宏,东京的智障儿童,等等。在这些纪录片中,他始终在探讨社会与人生的真实性问题,并形成了自己严肃持重、关注社会、思考内心、克制情感的独特风格。
是枝裕和几部剧情片最初的灵感都来自于他拍摄纪录片时期的积累。
《幻之光》
处女作《幻之光》,讲述了一个悲伤而困惑的少妇面对丈夫自杀这一事实所做出的努力,这个故事得自于他在拍摄《但是……在这个扔弃福祉的时代》时的经验。那位自杀的福利局官员的遗孀,她的挫败、悲痛、疑虑和孤独在《幻之光》中回荡。不同的是,是枝裕和在纪录片中直接追究了这起死亡悲剧的肇因,当他采访东京市政厅一位将责任推给下级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时,画面停在一座冰冷生硬的建筑物上,整个灰暗无名的权力体制遭到了是枝裕和镜头的审判。
而在《幻之光》里,死亡则被展示为一种隐秘的、无缘无故的欲望,女主角先后有两位至亲——奶奶和丈夫——平静如常地离开家门,莫名地去寻找死亡,女主角所有的悲痛都笼罩着一层黑色的无缘由。
纪录片《当记忆失去了》与剧情片《下一站,天国》,同样探讨了记忆对自我认同的意义。
《当记忆失去了》中,一位因医疗事故而脑损伤的人,无法贮存和忆起新的经验,每天早上都要重新面对与记忆中不甚相同的妻子和孩子,反复被告知自己已然失忆这个事实,生活之流被截住,只是不断重复痛苦的音调。是枝裕和连续数年跟拍这个男人,并追究了悲剧的原因:那不是一起意外的医疗事故,而是由于政府不透明的缩减成本政策,致使医生没有在手术后给这个男人注射维生素添加剂。这一状况同样导致了其他一些病人的脑损伤。
《下一站,天国》
两年后的《下一站,天国》中,是枝裕和以仿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一组超自然的故事:在去往天国的中转站,刚刚死去的人需要选择一段记忆,由那里的工作人员拍成电影,然后带着这段唯一的记忆被送往天国。
拍摄前,是枝裕和采访了500个日本人,他们的生活跨越了日本动荡的20世纪,一些人后来被选进剧组,与职业演员共同参与拍摄,职业演员的部分台词也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与故事。比如死后的“伊势谷友介”拒绝为自己的记忆拍电影,他认为,“我的记忆会结束,最终消失,变成想法。回看过去,我想我脑子里创造的,会比记忆更真实。在活着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是为了单一瞬间——‘此时此刻’——而活,现在看来,太痛苦了。”
是枝裕和将生死中转站设定成一个剧组,帮助从这里经过的人们细数眷恋、澄清思想,似乎生死之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追忆。这是个浪漫而充满想象力的主题:死去的人,展现活着。然而,是枝裕和赋予它的却是冷静而客观的表象。影片开始,工作人员平静地对逝者说:“或许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还是遗憾地正式通知您,您刚刚亡故了。”——所有的基调就已经被奠定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是枝裕和不断加深着对记忆与真实人生的体味。对于是枝裕和来说,记忆并非简单的记住,而是通过沉思反省才能获得的东西。追忆是一种艺术,是当人需要扩大自己的感觉时的一种技能。
《步履不停》
母亲去世后他拍了《步履不停》,带着许多他平生的印记。他感到仅仅记住一些往事是不够的,还要知道它们如何被表现,如何成为慰藉,“如果不把和母亲最后这段共度的时间中回忆起的东西做个整理,我就无法继续前进”,“我是个执着于记忆的人”。
在纪录片中,是枝裕和是历史、社会与制度的思考者,战后日本的都市景观与当代日本常常交错出现在画面中,形成历史的参照。在剧情片中,是枝裕和是个有城府的诗人,面对人性的复杂,他不想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一旦想明白了,可能我就会对这件事失去兴趣了。所以我故意不去找答案。”
拍摄《步履不停》时,是枝裕和“想要拍一个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故事”,“那部电影除了细节外别无他物”。这些细节,就像日本“物语”中夹杂着的那长长短短的是对白又不是对白、是独白又不是独白的“喟叹”。“细枝末节累加起来即是生活,这正是戏剧性之所在,我建构每一个场景时,都只依赖细节”。
《步履不停》
在拍摄现场,他潜心研究那栋老房子里的一切,让每样东西都带上情感。
“一间房子能做到许多事。从那个空间里传来的声音、色彩,让人联想起的味道,能得到许多的刺激。不论登场角色还是观众,都能感受得到在这个房子里独有的时间的流逝和堆积。”大人在这里谈着话,孩子们在那头玩闹着,后面的房间传来钢琴的声音。热闹的场景背后,刻意加入突然安静的瞬间……“我刻意尝试用声音去创造出空间。”
《海街日记》
在接受Lens采访时,是枝裕和会有意无意地回避谈论某个画面的意义,甚至一部电影表现了什么,却喜欢事无巨细地讲述每一个镜头的由来,那些有用或无用的琐碎的小心思、小设计,它们一点点建造起他要的世界。“在拍摄中我决定不考虑广泛的概念,诸如‘日本’或‘社会’。比如电影里的人物,我只关注那些他们可以用来投射感情的事物,像睡衣、瓷砖、牙刷,还有蝴蝶。我想要的是每一个镜头能够花几个小时去仔细地拍。”他说。
他相信细枝末节并不意味着无聊和缺乏感情。静观的态度包含对生命必然规律的认定和接受,虽然它不予人过多安慰,却是继续活下去的处世之道。
《鬼怪文豪怪谈4:后日》
对日常生活细节和场景的平静展现,使是枝裕和的电影带上日本传统审美中纯净、言犹未尽、极简主义的意味。
在他的镜头下,没有哪一朵花苞是未经允许便自行开放,没有哪一片花瓣是未经允许便自行飘落。然而,他却深知,“这个世界不按人的道理出牌”。他的人物少有强烈的欲望、极端的性格,他们都是生活中最为平常的人——即便承受着不寻常的变故。对于生活,他们是受力者,而非强力者,他们静静承受着命运之力,还要有所守持,完成自己,寂静得带上一种“弱道”之美。所谓“弱道”之美,不是软弱,而是以柔弱内敛的方式面对命运的强力,仍能有所持守、有所生长。
《花之舞者》
父亲去世后,是枝裕和拍了《花之武者》。“我与父亲之间本来很有距离感,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深入交谈。他的去世让我深刻感到生命的柔弱。清理我们的老房子时,重新发现了许多记忆,我意识到,即使在他死后,我仍能继续发展和生长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枝裕和的电影中充满了遗憾、丧失、困惑与死亡,而他的人物常常怀着那种“弱道”之美处身合围的乱象。它让人看到,正因了生命中这些重压,我们才是现在如此这般的样子。最重要的不是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而我们要怎样面对。
《无人知晓》
被一桩真实的社会事件所触发的《无人知晓》,主角是四个被母亲放弃、生活陷入困境的孩子。长子明独自承担着他并不完全理解的生存压力,几乎走投无路。这个男孩儿始终不曾哭泣,是枝裕和说:“他不该哭,哭对他是没有用的,而且,我不希望电影变得多愁善感,这是我的底线,因为我并没有打算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它可能会让人难过,但是最终,我想呈现的是一个男孩变得成熟。这个故事有它积极的面向。”
让观众在看电影时泪洒现场并不难,不过他对催人泪下这件事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克制与不煽情,从《幻之光》就已经奠定了基调。
《幻之光》
《幻之光》的女主角由美子在少年与成年时代先后目送奶奶和丈夫离开,由美子反复被抛进这种无缘由的死亡的黑暗。然而,是枝裕和没有让由美子痛哭流涕,哪怕是一次。由美子一袭黑衣,在地板上、楼梯上、电车里始终面无表情、一动不动,镜头悬搁着在静止的场景之间不断切换,仿佛时间停滞,烘托着由美子被悲痛压垮而无法行动与思考的处境。是枝裕和无疑十分了解静谧的力量,静谧可以比最大声还大声,也可以比最弱还弱。
他也很少在充满强烈感情的画面里使用脸部特写。他的摄像机总是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有间隔地拍摄情感高潮。借助戏剧性来表达悲哀和愉悦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如果只能靠这种”说明”式的手法来表达,会扼杀人物和人生的基本真相。是枝裕和无法忍受那种不借助台词和音乐就不传达任何意义的影片。着手拍摄《空气人偶》时,他的目标甚至是一部默片式的电影。
《空气人偶》
是枝裕和对人没什么好感,“人类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说。对于同样拍摄家庭伦理片的两位前辈大师——小津安二郎和成濑巳喜男——是枝裕和坦言,他更容易认同成濑巳喜男,因为“成濑对人性的认知更为黑暗”。他甚至对自己也没什么好感,觉得自己是这一代里“很没用的男人”之一。《步履不停》中,阿部宽扮演的“小家子气又没出息”的男人形象,就是是枝裕和对自己的反思和嘲讽。
然而,是枝裕和又是个温柔的人,他对他反感的人类充满同情。
就像在《空气人偶》中,人们和他们的生活都是“中空”,所以满大街都充满着疲惫和隐忍的行走,外在的生活带不起内心的感动。而他也同时表达了“空缺其实也存在着其他的意义,与他人邂逅相遇的可能性”。
他疼惜自己电影里的人物,终会给他们一个出口。在许多影片的结尾,他的人物都能敞开体内原始的温柔,是其所是,爱其所爱,面对生命之殇有所释怀。问题并没有解决,却不再是阴暗的死角,心房里,窗帘被拉开,有阳光照进来。是枝裕和说,我想看着人们如其所是,如此而已。
《海街日记》
Lens:为什么想拍电影?
是枝裕和:本来进大学是想写小说的,进去后觉得文学没什么意思,当时早稻田大学附近有很多电影院,我在电影院里度过了很多时光,后来就决定去拍电影。
Lens:最早意识到死亡是什么时候?
是枝裕和:一同生活的祖父去世,大概是6岁的时候。当时的祖父是喜欢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亲戚们都不喜欢他,但是祖父过世后亲戚们来参加葬礼都哭得像泪人儿一样,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平时那么讨厌他竟然可以哭成这样。从那时起觉得人是一种会有内心黑暗面的动物。
《比海更深》
Lens:你对孩子的世界有非常细腻的感知,是怎样保持这种感觉的?
是枝裕和:一个是记忆,一个是观察。主要是观察,认真看孩子的表情动作,听他们说的话。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变得更方便了,每天都在一起,每天都能看见他们。
我毕业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在一个小学,花了三年时间去拍那些孩子、家长、老师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三年学习到的非常之多,也是之后为什么喜欢拍小孩子的原因。
小孩子做事情没有什么目的性,怎么在电影中表现他们这种不受控制的目的性呢?我就常常让他们跑起来。举例来说,《步履不停》里一家三口回老家,男孩子跟在后面给妈妈拿伞,他就一会儿看看水沟,一会看看树叶。大人走路有目标,回老家就是回老家,而小孩却生活在那一刻的空间中,虽然他看水沟看树叶好像没什么意义,但如果不这样,他就成了大人的附属品。表现小孩子的独立空间是我这样拍摄的目的。
我比较喜欢侯孝贤那种拍摄现场的风格,他是那种如果拍孩子就会和他们一起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储蓄了很多感觉,再正式拍时,这种感觉会持续下来。我不太喜欢指挥演员,尽量让他们自由发挥。
《奇迹》
Lens:电影《奇迹》里面,面对火山喷发,小孩子比大人更淡定,大人们出现感情问题时,好像更被动,反而是小孩子在努力弥合这之间的裂痕?
是枝裕和:这是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小孩子其实是非常冷静地看着大人的世界,比如大人吵架时做什么才能让爸爸妈妈和好,小孩其实是在算计这些问题。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把它映射到了电影中。
Lens:现在日本,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不是还是母亲?
是枝裕和:比以前好多了,公司为重、事业为首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变淡了一些。
《步履不停》
Lens:《步履不停》里的中年男主人公,相对于老父亲来说,没有能打拼一份家业,也不会帮妻子忙,似乎很无用,这是当下这一代人普遍焦虑的问题吗?
是枝裕和:这主要是我个人的问题,不过这一代人也有这种共同的弱点。因为上一代人比较有功绩,相对来说这一代日本人就觉得自己有点无用、弱小,也觉得害羞、羞耻。
Lens:对弱者是不是有特别的同情呢?
是枝裕和: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一种共感。我很喜欢成濑巳喜男导演,他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弱者、不中用的人,但这些作品都没有否定他们的存在,不像美国的电影,每个人最后都要成为强者,成濑的作品却是肯定弱者的存在。我的作品里如果说是有一点亮色,也是基于对这些弱者的肯定。
《如父如子》
Lens:日本大地震时,有报道说,当时男人们发平安短信是给妻子而不是情人,大家是不是都在反思现在的家庭观念,你怎么看?
是枝裕和:其实也应该给情人发条短信。这种时候不应该分高低贵贱。
我认为地震发生后日本价值观的范围反而是缩小了。本来是共同经历了灾难,大家应该一起共同面对,但是反而缩小到只关心自己和家人,虽然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是关心还在幼儿园的孩子。这种缩小不太好。
《小偷家族》
更多精彩关注微信公号"WeLens"、微博"WeLens"
更多关于Lens读物及购买详情请戳>
更多介绍请前往Lens官网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文字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后台
识别下方二维码,关注“Lens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