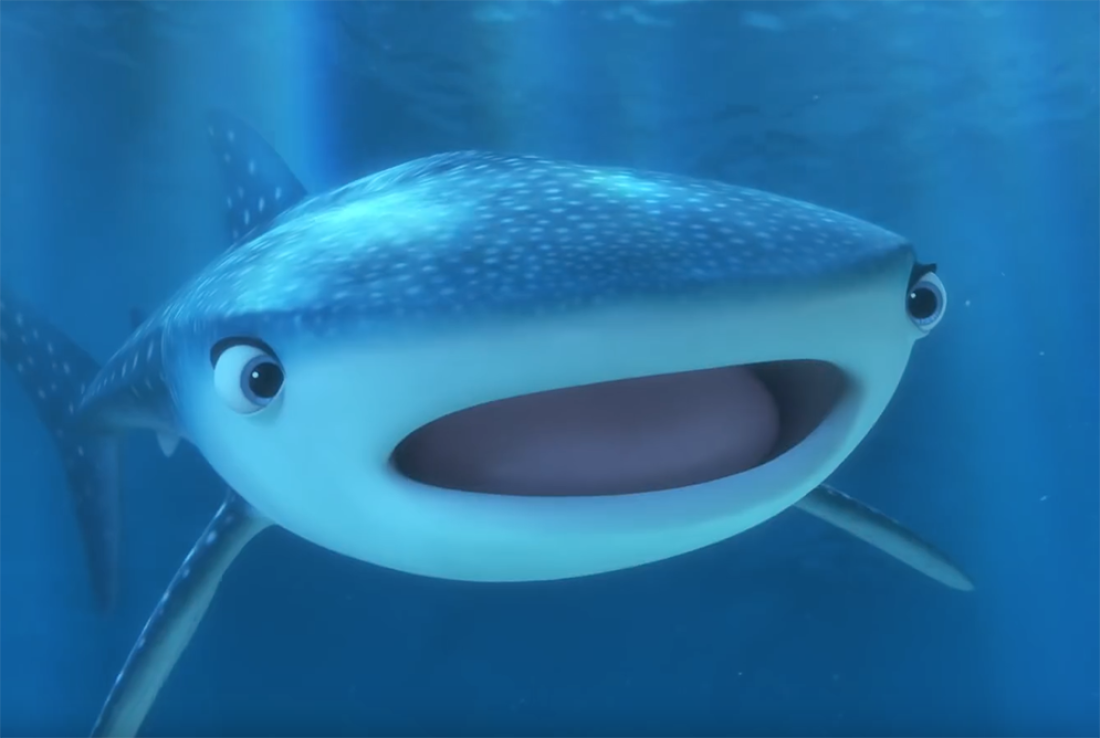阿修死了之后我继续自己一个人活着,活得久了变成一种习惯,就算我不愿意,但事情就是会这样发展。
傍晚的时候醒来南北韩已经开战,战场就在我的脑袋,一颗炮弹从天灵盖冲向我的鼻腔,千万发子弹穿过眼窝,撞到头盖骨又反弹,出不来,钢弹碎片散落在脑液上飘浮,有的半空就降落扎在血管里。
昨晚喝得太多了,现在我得用一只手托着脑勺才能从床上坐起来,也就只是坐起来。
细弱的脖子承受不住这颗盛满酒精的脑袋,跟着视线在房间里左右摇晃,最后我试图把头正摆在木质床板上,强迫自己不要去听耳朵里停不下来的坦克轰鸣。
一切都安静下来之后我才想到阿修已经死了。
他在昨天凌晨从另一家酒店的顶楼掉下来,目前还不确定是不是自愿的,我想应该不是,因为他没有跟我说过他想要去死。
前一晚我在出店门前遇到他,和他一起走到店门口,他故意选在门口的摄影机面前作势搂我的腰。
“我已经报离职了,很快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牵你了。”他说。
喉咙被哨烟烧得几乎灼裂,我努力保持对焦走到厨房,一股脑喝完了热水瓶里所有的水,稍微冲掉了瓶口的口红印之后,我又煮一壶水打算给自己泡碗面。
这段过程手机已经响了三次,另外还有几次是短讯音,几乎都是客人的问候,有一封是昨晚最后一桌客人,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没有人会在意漫长生命里无意义的两个小时。
进包厢之前我就已经喝了很多,里面总共有四个人还是五个人,他们点我坐下,接下来的事我就没有印象了,反正玩游戏、唱歌、喝酒,总之就那样,可能我还吻了某个人,所以天亮前他才跟我要了电话号码。
我回了电话给小芭。
“起床了啊?你今天有报班吗?“ 还没出声就听她扯着没开嗓的声音问道。
“有啊,我要先去一下夏姐那边,我想少喝一点,我快要把自己喝成个智障。“ 我走进厕所看着那只掉落在马桶里的高跟鞋,没看到另一只。
“你要毕业啊?“小芭调转了音量,只用我们两个听得到的大小。
“想休一个礼拜,反正先听夏姐怎么说吧,我脑袋快炸了,去店里再说。“ 我用衣架把那只鞋子勾出来,在水龙头下面淋了一会儿,然后丢到垃圾桶。
勉强把三口面条塞进食道之后,我冲到厕所抱着马桶将近十五分钟,面条跟威士忌都呕完之后喉咙开始渗出血丝,混着绿色的胆液,终于不再感到头晕和口渴,脑袋暂时休兵了,我这才冲了个澡,试了几次才将隐形眼镜顺利地黏到眼球上。
“那你的另一只鞋呢?“ 中午的办公室只有几个助理,我跟夏姐说了高跟鞋的事。
“我不知道啊,会不会我根本就没有穿回家?“我努力在回忆,就是想不起来。
“既然不想喝那么多的话你就调午场吧,可是台数会差很多哦,生活上应付得过来吗?可以的话就看要下一档还是下个月开始吧。“ 夏姐故作关心地问,一边看着这一档的台数可惜地叹了口气。
“我不想转午场,我想休息一个礼拜。“我捏着皮包一角。
“钱够用吗?“夏姐翻寻着小姐的借条。
“欠公司的这礼拜就可以清掉了,所以下礼拜开始休。“ 我瞄了她一眼,一边滑着手机的短讯,是小芭询问会面结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去设计师那边完妆后就打算直接到店里。
阿修掉落的地方还挂着警示带,地上深色的血迹没有被清掉,染在粉红砖道上,不仔细看的话就像从谁嘴里倒下的槟榔汁而已。
我抬头看向楼顶,想像阿修在那里经历过什么:他有喝酒还是吃药了吗?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不小心爬上半身高的围墙,然后不小心掉下来?天刚亮的那时候,没有人能发现他吧,他是有意识的死去吗?
我蹲下深吸了一口气,想试试能不能闻到他的香水味,我知道他平时工作都会喷香水,但什么牌子什么调性的闻不出来,我们身上混杂着空调、酒精、槟榔、毒品所混合出来的气味;碍于规定我们无法距离彼此太近,只有偶尔在走廊上经过然后闻到那股擦肩而过的香味。
有时候他会轮职站泊车台,在我准备上班的时候他会从泊车台下伸出手来,轻碰一下我,然后视线一路看着我走进店里,这时间他身上还没有被店里的气息感染,我甚至可以闻到他背心刚熨烫好的蒸气味,如果有下次我想靠近他,好好闻他。
没有下次了。
“欸,怎样,你有跟夏姐讲了吗?她怎么说?“ 我衣服换到一半小芭就凑过来问道。她今天上了很夸张的蓝色眼影,贴了两层假睫毛,眼尾的部份还黏了一根羽毛,很像以前红包场歌舞厅台上的歌者;发型是整头的大波浪,还有两撮像蟑螂须一样的发丝从两颊旁边垂下来,我一直很庆幸没有去她介绍的造型师那边打理我的造型。
“休一个星期啊,夏姐说可以。“ 我试着把小芭的蟑螂须塞到她的耳后,但没有用,发胶已经把那两条固定住了,我把眉头锁了一下。
“你不是有预支,都还完了?“ 小芭端起她两边的发须看了一眼,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礼拜可以还清,休息回来后应该会再预支一点。“ 我对着镜子稍微整理了一下就要走去打卡。
“欸对了,上礼拜那个老胖子今天晚点要框我出去吃饭,还有他朋友,我怂恿看看能不能叫他朋友点你,这样今天就不用喝了。“ 小芭随我一起走到了卡钟打卡,然后边走去看台。
“我又没配,如果纯的我OK啊,看他们吧。“ 我看着拿托盘走来走去的少爷们,阿修不在大厅,酒柜跟吧台那边也没有,走廊上只有几个干部守在包厢门口。阿修已经死了。
茉莉姐站在包厢门口招呼我们快进去看台,走近后她一手把我挡在门外。
“小芭,你进去看就好,小蝶不能看我的台。“
我转过身翻了白眼,走回控台回报,然后就进了休息室。
“欸欸,茉莉姐为什么不让你看她的台?“小芭没有被点上,她小跑步回到了休息室。
“有次跟她客人呛起来了啊,反正她就不让我上她的台了,已经很久了,上礼拜她不在,我还不小心被点上,坐了一个小时被她发现还是把我给叫出来了,反正她客人也没有好咖,不坐就不坐呀。“ 我拿起桌上的薯条嗑了起来。
“茉莉姐的客人整晚大概占了三成吧,这样损失超大的,你有道歉吗?“ 小芭试探的问。
“是谁的错她心里清楚好吗,她只是为了要留住那个客人,所以把我牺牲了,我干麻要道歉,而且拜托,我在其他干部那边还是很抢手的。“
三个月前我噘着嘴被赶出包厢的时候,阿修刚好也在那条走廊上。他不应该单独跟我说话,但还是问我怎么跑了出来,我说客人要我出来罚站,他“靠“了一声卷起袖子就要进包厢,被带台给拦下;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是谁,以为他跟这包厢里的人原本就有过节,那个时候我没来得及说谢谢,到现在都没说。
名牌上写着他的名字叫阿修。
快九点的时候有个老客人,通常他会和他那个大嗓门朋友一起过来,今天只有他一个人,他上身的釦子几乎开到了肚脐,进门的时候他正往九宫格里斟满了酒。
“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看我进来他随手拿起一个酒杯就往嘴里浇,随后满上。
“怎么那么巧,两个心情不好的人一起喝酒,那不就负负得正了。“ 我在他旁边坐下,右手顺势滑进他的衬衫,侧过身子环抱住他,下巴靠在他的锁骨,让他胡子在我额头上撕磨,我喜欢坐在客人的右手边,因为他们的左手通常没有右手来得灵活,而他们也懒得抽出被我死死抱住的右手。
“哟?红牌也会心情不好?是今天还没喝吧?“ 他拿出两个酒杯敲在我面前的桌上,我一手一杯灌进喉咙。
“那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呀?“ 我对着他眨了眨眼。
“我觉得这样每个礼拜来找你,太累也太麻烦了,你看我都还没找到地方住,就先过来找你了,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偷情,可是男未婚女未嫁,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为什么要这样。“ 我看着角落边他的行李,他刚就是这样扛着两大箱行李进到酒店。
“快了,我也不太想做了,想要跟你定下来。“ 我没有完全骗他,我是真的想要定下来,只是不是跟他。
“真的吗?你可不要骗我,你想好了吗?是要我到台北我们一起找个房子,还是你来桃园跟我住?“ 他看起来像是中了彩票的街友。
“住哪我还没想好,可能我下去跟你住吧,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整理,反正我下档前一定会你说的啊。“ 我给他递上了酒,再探出舌尖把他嘴里的酒讨回来。
两个小时后我离开包厢,用大厅的镜子补了口红,然后回到休息室,小芭九点多就传了讯息来。
“他们不纯出,下次有局再找你,我今天不回店了哦,高跟鞋记得要穿好。“ 我松了口气,今天突然很不想出去。
接下来几台都是老客的桌,没喝多,阿修没有进来送过湿毛巾;走廊上冰柜的位子有个少爷弯着腰在捞冰块,完事后他转头看到我便低下头绕个路走了。
转角边有两个少爷在用台语说着什么,我听到好像阿修的名字,另外还说了“四个人“跟“丢下去“,我转弯探头看了过去,是两个常见的少爷,没说过话,我见过阿修跟他们把湿毛巾互相扔来扔去,阿修当时还扔了一条在我身上,那两个少爷看到了我没有再继续说刚的话题,也就散了。
茉莉姐的事情过后几天,阿修拿着两个冰桶在这边瓦着冰,我排队等着看台,正好就排到他身后的位子,他转头看向我,用很急,很快的速度对我说: “要是有人再欺负你就跟我说,以后我罩你。“ 说完后他随即转身离开。
我现在特别想要被人欺负。 我跟着其他小姐去控台报了下班,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和卖花的阿姨买了朵红色玫瑰,回家前我想再去看看阿修。
警示带一端已经掉落,浅黄色的胶带被几只鞋印踩踏,红砖上的血渍颜色明显淡了许多,面积稍微向外扩张,看来两旁的店家有做过泼洗。
我站在血渍边缘,伸出一只手浮盖在血印上头,然后发现这是我和他目前为止最近的距离。我把玫瑰插进了树下的土壤,双手合十想对他说些什么,但我脑中一片空白。
“谢谢你,阿修。“ 最后我说。
我难得睡了好觉,谁也没有梦到,在太阳还没爬到正上空就醒了过来。下床前就应付完几封短讯,随后拨通小芭的电话,昨天那双临时凑合的鞋挤得双脚实在胀痛,我得在上班之前给自已换双高跟鞋。
“亲爱的起来好吗,陪我去买高跟鞋,我还要去吃饭,我饿。“ 我拿着话筒撒娇,用的是对客人那招,小芭也吃这套。
“还吃,我从昨天晚上九点多吃到早上八点欸,我胃里的东西都还没吐出来又要吃啊。“ 小芭的声音还很沙哑,咕噜咕噜的喝水声沿着电话线传过来。
“那陪我吃就好,我真的很饿,我还没有鞋子穿,上不了台怎么办呢?“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饿,但我觉得很空,很空,试试看如果吃到胃里的东西够多,那它们会不会满到我的心上来?
半个小时后我来到小芭家楼下,也是另一家酒店门口等她,我刻意避开了酒店放在天花板的监控器,选择了墙柱旁边的位子等待。
我没有上妆,那天也是这样,突然想吃这里的日式拉面,一起床就走过来了,经过这里时阿修从这间酒店的楼梯上跳了下来,他看起来兴奋极了:
“哈哈,我看那画面就知道是你,你素颜我也看得出来,我就知道是你。“ 他张开手挡在我的面前,穿着那件酒店的背心。
“你怎么这时候在这里啊?“ 我指着他纳闷,马上又察觉自己的确是素颜,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
“来来来,快点,你来,跟我上来。“他像一只讨到香蕉的猴子一样雀跃。
我随他走上了楼梯,楼面上只有一张类似吧台的桌子,上面摆了四个荧幕,每个荧幕上都切割成四个监视画面,还有两张红色椅子。
“你坐这边,就这边,对,今天你就坐在这里,我坐你旁边,我坐这边,嘿嘿,你今天走不掉了,可是我们不能离太近,我要拉开你一点,就这样,好,就这样看荧幕就好,反正这时间也不会有临检。“
阿修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忙着张罗,我看起来,不就是两张椅子很简单的事情。
“我坐这边干麻?“ 虽然困惑,我还是听话盯着荧幕。
“陪我。“他简短两个字,没了刚才的囉嗦。
“哦,可是我很饿,我是出来找吃的。“ 原本已经坐在椅子上的阿修跳了起来,十分钟后买了碗面放在我面前。
“欸,我常看你都一个人。“阿修托着腮侧头看向我。
“不然要几个人?“我边吃面不解的问。
“不是啊,就觉得你很孤单,所以我才想要保护你。“ 阿修说。
“你的梦想是做超级英雄?“ 原来保护我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孤单。
“我的梦想是变富有,离开这里,可是还是会继续保护你。“ 阿修的个子不高,穿上高跟鞋的我大概跟他一般高,但他的嗓音跟志气却很高。
“你是要负担家计吗?“ 通常同行间不太会过问彼此进来这行的原因,一是怕抓破对方的伤口,二是怕抓破自己的伤口。
“当然啊,我们哪个人不是为了要负担家计。“ 阿修把头转向荧幕。
“我不是啊,应该说不完全是。“ 我笑着说。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了找个男人嫁了?“ 阿修又看向我。
“为了之前男人的赌债。“ 我尽量表现得不在乎的样子。
“那他人呢?“ 他问得很急。
“跑路了。可是他妈妈还在,我如果不帮他还,那些人就会去找他妈妈。“ 我在心里盘算着还剩下多少债务。
“你家怎么说?“阿修问。
“我是孤儿。“ 我从来都不知道父母是谁,所以我更在乎每一个阶段陪伴我走过的人,跟他在一起时,他和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太夸张了吧,这关你什么事啊。“ 阿修的耳机里面传出嘶嘶的杂音,他把耳机拿下来放进背心胸前的口袋。
“你又为什么要做这个?“ 除了夏姐之外,我没跟谁提过这件事,连小芭都不知道。
“我家需要钱,我白天在这家盯着这些荧幕兼差,晚上去你那家做少爷,这边白天就你看到的没什么事,只要注意有没有临检,还可以稍微小瞇一下,不要被发现就好。“ 阿修耸耸肩,拿起纸杯喝了一口水。
“是需要很多钱吗?“我试探地问了一下。
“很多,可能赚一辈子都不够用吧。“ 阿修把卫生纸推到我面前,帮我把吃完的餐具收拾拿去丢掉。
“你没有交女朋友吗?私底下?“ 我知道有些少爷私下会跟小姐有往来,甚至同居,只要台面上不被发现就好。
“没有,我赚钱都来不及了,没空搞那些有的没的。“ 他用一种轻视爱情的口吻。 “你放心我没有要追你,我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的,我只是觉得你跟我很像,有着一些秘密。“ 他继续说道。
“谁没有秘密啊,何况是在这种行业。“ 那瞬间我觉得阿修比他外表显露出来的还要更加深沉。
“总之就是觉得在那里我要保护好你,好像你是我妹妹那样,你只要出事,就像我自己出事一样,搞不好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哦。“ 阿修笑得很开心。
但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护我了。
思絮回到身体里,我走到摄影机下方,直视着镜头,阿修没有再冲下楼来找我,跑来的是扶着额头的小芭。
“哦宝贝,我的头真的太痛了,我们可以速战速决吗?“ 小芭哀求着,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猛灌。
“那买鞋就好,我自己买东西回家吃吧。“说着我便快速走到了不远处的鞋店。
“欸,你知道我们店里有个少爷前两天跳楼吗?“ 随意看了几双鞋,小芭八卦起来。
“有听东哥说。“ 我好奇小芭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小芭吊起了我的胃口。
“你不就说了跳楼吗。“ 我不想说太多。
“不是,他不是自愿的,好像是抓到诈赌被人家丢下去的。“ 小芭好像在瞄述一部精彩的电影情节。
我的双腿突然一软,心里好像有颗未爆弹被按下了按钮,阿修大笑的样子浮现了出来,彷彿按下按钮的人是他。
“你怎么知道?“ 我问小芭。
“昨天胖子带出去的那群有一个人在场,是赌博的现场,他们在包厢里赌,但不是他丢的,他说有四个人把那个人带到顶楼,然后隔天那人就死了,坠楼死的。“ 小芭随便拿起一双鞋子套到脚上,对镜子照了一会儿又放回去。
“那警察没找他们?“ 我尽量装作不在意的口吻问道,一边翻开鞋子确认尺寸。
“有用监视器找到那四个人,那四个人把他带到顶楼,不是硬押那种,就是那个人跟着他们,到顶楼后就没有监视器了,他们说只打了他一顿,但没有丢他下去,打完他们就走了,那人也没有跟他们下来,之后他就坠楼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四个人都是这样说,超邪门的。“ 小芭对着镜子整理起凌乱的头发,一边跟我说。
“但是胖子那朋友说八成是那几个人丢的,他们做事从来都不手软,何况诈赌这种事情是大忌,他们不会放过他的,只是没有监视器,他们又统一口径,警方暂时也没办法拿他们怎么样。“ 小芭还在继续没完没了的说着,没注意我停不下颤抖的手。
我的内心兵慌马乱,我想过各种阿修跳楼的原因,但没有想过是这样,原来他不是自己要丢下我的,而是被逼的。
战争停了下来,一个小孩全身脏兮兮的在战场中央,一步摔一步跌地翻找亲人踪迹,身体染上士兵和百姓的血污,跟她一般高的箭矢戳到已经凹陷的脸颊,最后被断肢扑倒在城门边上,盯着放眼望去的尸首狼藉。
随便挑了两双鞋,我就放小芭回家补眠了,一个人来到阿修最后躺着的地方。和昨晚没什么不一样,只是警示带已经变成灰黑色的了,除了依然伫立在土中的玫瑰,这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可是它确实发生过什么,除了我之外,还有人会记得吗?
半年后、一年后,阿修这个人就从这世界完全抹除,好像他不曾来过那样,原来一个人要消失那么简单,只要“砰“的一声,他就不再存在,回忆呢?约定呢? 我很想要知道真相。
今天很早就到了店里,阿修不在泊车台,我走进东哥的休息室,他正在吃饭,来之前我已经打好草稿,想着该怎么让东哥相信我。
“东哥,我可以问你些事情吗?“ 我走到东哥身边的椅子坐下。
“问啊。“ 东哥利落的回道。
“我想问阿修的事情,可以吗?“ 我有些不带底气,毕竟这种事情,干部一般不太会让小姐搅和。
“阿修什么事情?“ 东哥迟疑了一下,把盒饭盖起来转身面对我。
“就是,他是怎么死的?是被推下去的吗?你认识推他的人吗?“ 我一次把想问的都问了出来。
“他跟你有关系吗?“ 东哥看了一下手表。
“我有个朋友是他的干妹,我答应要帮她问清楚,只是想知道原委而已。“ 我直视着东哥的眼睛,想要得到他的信任。
“我知道的也不多,我那时候会跟你说他过世了是因为我看出来你们有些交情,警方那边是用不慎坠楼结案的,有几个人有嫌疑,不过都被排除了。应该是吃了药又被人打,头晕了才掉下去,这件事你也不需要到处去说,好好上班就好。“ 我真的不知道阿修有吃药的习惯。
“那你知道嫌疑人都有谁吗,有我们店里的吗?“ 我不放弃地问道。
“每个人都是几家店跑来跑去的,我没有去注意,好像有两个是包子哥的客人,常常来,昨天也有来。好了,我要去带台了,你知道就好了,没事了,人已经死了,叫你朋友也放宽心。“ 东哥拿起对讲机起身就往大厅走去。 还好是包子哥,不是茉莉姐。
八点整第一桌就是摇桌,也就是吃摇头丸的桌,上班时间我不反对自己吃药,药会醒,比宿醉好。
今天吞了一颗等大半个钟头还没什么反应,只有手心微微出汗。包厢里的灯已经全暗了下来,电视没有画面,一开始放的还是古典轻音乐,桌上点了三个蜡烛,墙壁上可以看到蜡烛忽高忽低的剪影,大家都没有说话,牵着彼此的手闭上眼睛。
六个客人六个小姐,四十分钟后他们逐渐失去理智,好像只有我还清醒,不到一个小时已经有一个男人在地上爬,可能是正在征服百岳,他手指在地上挖着,想从石缝中固定自已向上爬去,一个小姐蹲在他旁边摸着他的头发。
有一个小姐坐在客人腿上,上半身向前两手扶着空气,那个客人把身子左右大力摇晃,发出呜呜的声音,陡然停下来后,没一秒再上下抖动,小姐俯首闭眼,脑袋不经意的跟着晃动,嘴巴开开的但没有发出声音,原来是在坐云霄飞车。
我身边这位看起来才二十初头岁,他一手捏着我的大腿,手脚拼命抖动,他闭着眼睛摆来摆去,嘴里喃喃的说着什么,我靠近去听,他正在说“北七哦,伶北每乎啊,卡紧拿来。“ 我的大腿被他捏到全都是水汗。
我用烟管勺了些K做了根烟塞到他嘴里,他吸了一口又把烟拿给我,我也吸了一口,脑袋里的泡泡纸“啵“一声破了。
我看到那扇小窗户,一扇我每次吃了药就会出现的窗户,在两层楼梯之间,也许是最上一层,窗户外面阳光很大,但我走不到那里,我就站在原地,看着那扇窗户,每次我都想着只要我能看到那扇窗户外面的景,我会到达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层次,但这次一样看不到,我退了回来。
视线回到烛光忽明忽暗的包厢内,我看到阿修拿着烟灰缸还有可乐进来,他没有抬头,但我知道是他,就是阿修,他说“老板好,送可乐。“,没有人理他,我帮他把拖盘上的可乐还有烟灰缸拿下来,他瞟了我一眼,手背轻轻碰触到我的手指。
“还好吗?“ 我问他,他的头抬起来了,又看了我一眼,没有表情,随后拿了装满烟蒂的烟灰缸低下头退到了门口,我没见到他走出去,就觉得他一直站在包厢门口,在那边看我,好像机器人那样,走到门口就没有电了,垂着头站在那边有些沮丧。
我也看着他,他身上应该没有伤痕,制服也像刚烫好的那样,即使包厢黑漆漆的,我仍然能看得清楚他,只看得清楚他,看不到包厢里的其他人,其他人都不见了,这包厢里只剩下我和站在门口的阿修。
我又吸了一口烟,接着把烟熄在他刚换新的烟灰缸里头,再抬头,他已经不见了,其他人又回到我的视线。
地上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再爬行,他躺在地上处大字型,脑袋还在晃动,也许他已经到了峰顶,他身旁的小姐已经回到了沙发上,拿着可乐喝着,视线却没有离开登顶的男人。
最靠近门口的那对男女正在拥吻,男人的手在女人的裙子里面胡乱搜寻,像在家门口翻着包包找钥匙,女人一边吻着他,一边想把他的手挪开,但没有力气,最后身子只能软绵的任他使唤。
我缠起旁边那个男人的手,闭上眼睛,靠在他的肩膀上,他还在咕哝着什么,是台语,我听不清,我跟他说“你醒醒“,他撇头看了我一眼,又把半颗药丸塞给我,他以为我醒了,我犹豫了一下,又吞下了那半颗,也许这次阿修会跟我说话了。
五分钟后我全身都开始出汗,手脚开始有麻痺感,我没有感觉我触摸到的任何东西,我也不知道现在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那扇窗又出现了,可我一样没有往前,我还是站在那里想着,有一天我会看到窗外的东西。
往下走的楼梯变得含糊不清,下面隐约也出现了一扇窗户,那扇窗户外面是黑的,我一点都不想看。
我听到有几个人从楼梯下面往上走的声音,我看到他们了,有五个人,阿修走在最前面,他的全身都在摇动,眼睛闭着,样子像触了电的活尸,重音乐让楼梯跟他们五个人都触电了,他们一蹬一蹬的走上来,然后在上层那扇窗户停下来,他们节拍性的把阿修按在窗户边,阿修坐下来了,盘腿坐着,身子仍在上下震动,随后那四个人就往回走,下了楼梯,剩下我跟阿修,阿修没看到我,我又退了出来,还关上了通往楼梯间的防盗门,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我突然很想抱住什么,于是身体绕上了身边的人,我跨坐在他腿上,紧紧抱住他,他也很用力抱着我,我觉得很舒服,不去想刚刚的事了,我的身子禁不住的蠕动,嘴里也不受控的呻吟,真的太舒服了,好像冬天里被热水包住的感觉,我收起手把自己蜷曲成一个婴儿的样子,男人环抱我边拍着我的背,之后他的手紧紧抓着我的头发,但我没有感觉,只知道他正在揉捏我的发尾。
一个小姐突然尖叫了起来,很大声,比音乐声还大,我听出来了她是在唱歌,旁边那个男的摇着铃鼓配合着他,还一边拿铃鼓敲着自己的头,大家都笑了,笑得傻里傻气的,我也笑了,这是我这几天以来,头一次觉得自己好些了。
包厢的灯突然大亮,电视出现画面,一首中文流行音乐的广告,所有人被唤回现实,时间到了,我看了旁边那人的手表,已经过了午夜,在这包厢待了快五个小时,我看到了阿修两次。
我回到休息室喝了华姐买来的牛奶,大口大口灌下,然后就到厕所去挖吐,其实也不用挖,牛奶很快就把毒品从胃里推了出来,我听到广播在叫我的名字,有人来点台,我又呕了两分多钟才出去,在包子哥的催促下进了包厢,是包子哥的台。 也是个老客人了,我的药还没完全退完全,扑向了其中一个客人的怀里,他拿了杯水给我。
“你又嗑药了啊,是不是还好我们今天有来,不然你不知道会被谁给带走了。“他叫小四,身材很瘦,抱起来都是骨头。
“四哥哥,我好想你呀,你们上礼拜没来,我整整醉了一个礼拜呢,还好你来了。“ 我把他搂得更紧。
“少来了吧,你四哥哥每天都在唸你,你平常也不会打电话给他,要他亲自过来才能见你一面,一点诚意都没有。“ 旁边一个老头说道,他是小四的亲哥哥,两个人形影不离,工作休假都在一起。
“四哥哥,他凶我。“ 我把头埋进小四的胸膛,抓着他两只手抱着自己。 “反正之后我们就住在一起了,现在我来找他有什么关系。“ 小四顺势把我搂住,我的身子还是忍不住随着音乐晃动,对着他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没有了音乐和灯光的加持,药很快退得差不多了,和小四对唱了几首情歌后我开始喝酒,包子哥也进到包厢一起参与,几人玩起游戏。
“事情怎么样了,还要跑管区吗?“ 老头今晚输得最多,把酒干了他问包子哥。 “今天早上还有去,应该是没事了,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我只是给他们开桌。“ 包子哥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一饮而尽。
“那几个不都你熟客,到底是不是他们干的你不知道?“老头把骰子骰了出去。
“他们最近有帐一直收不回来,可能是这样心情很不好,才想没事找事;林容修又不是真的诈赌,他们只是找借口拿个人出气而已,那几个又不笨,没事杀人干麻。“ 包子哥骰出了豹子,拍一下桌子大吼一声“喝“,我们其余四人拿起酒杯倒进嘴里。
“你们是在说我们店的少爷吗?“ 坐老头身边的那个小姐问道。
“你认识啊?“老头狐疑地问她。
“不认识,有听说,人家说是嗑药坠楼,不过不知道和你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那小姐看了一眼包子哥,不太确定此话该不该说。
“他有嗑药?“这次换小四说话了,我拿起水杯递给小四,小四推开我的手,吻了我一下。
“之前没看他吃过,他白天晚上都要上班,那天倒是有吃,其他人没吃,所以他们才想要整他,因为只有他脑袋不清楚。“ 包子哥倒是没怪那小姐乱讲话,把他知道的说了出来。
“平常都没吃,突然来一颗,难怪会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老头说道。
“他说那是他的幸运药丸,吃了会带来好运,你们看,果然就带来好运了吧。“ 包子哥嘲讽地说着,把碗公推到一边,靠在椅背上翘起腿来。
“你看,吃药多不好,以后药桌就不要上了吧,不然真的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药效退了吗?“ 小四低头看了看我,从桌上拿一颗蕃茄塞到我的嘴里,我点点头,勉强挤出笑容看着他,他没看出来我有多僵硬。
“主要也是查出他有毒品反应,所以我那几个客人才会没事,他嗑嗨了,自己跳下去,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所以小蝶你要注意,你常上的几桌药都吃得很凶。“包子哥很认同小四的话,转头看向我。
“可是常吃的话搞不好还没事,他那是平常没吃,所以控制不了自己才这样吧。“ 另一个小姐说道,她拿起摇控器点起歌来 。
“你这么有经验,我现在喂你吃药然后把你带到窗户边看你能不能控制得了自己。“ 老头瞪了她一眼。
“重点吃了药不要跑到窗户旁边或顶楼就对了。“ 包子哥哈哈大笑,刻意地打了圆场。
我在天微亮的时候走出店里,泊车台是空的,没有人。
我走到阿修最后待过的那栋楼,一些客人彼此搀扶在门口或站或坐,还有些妆已经晕开的小姐憔悴向外走出来,和刚上班时的光鲜亮丽完全不同。
我坐了电梯到最顶层,然后再往上走去,调查也许才刚结束,防盗门没有上锁。
我使了一些力才推开防盗门走出天台,踢开门口一块长满黑斑的红砖块,拿出一颗下班前和其他小姐买的药丸吞下,靠着水塔坐了下来。
地上有一袋槟榔包装,用过的毒品针筒被丢弃在靠近门口的金炉旁,一张报纸在地上被风嘶嘶地磨擦滑动,在水洼上停了下来。我盯着对面被风吹到褪色的广告广告牌,此刻挤身世上最后一块岛屿,最终我也会沉没。
天已经完全大亮,我的眼皮被晒得下垂,全身毛孔都在吸收着热气,水泥地已经被煮沸,咕噜噜地冒着水泡,靠近围墙的地方还有一波一波被烧灼的浪。我看到了阿修。
一个阿修、两个阿修、三个阿修、四个阿修...... 阿修从各个角落走出来,还有一个艰难地从水塔里往外爬,他们有的坐在地上摇晃,有的坐在围墙看着楼下,有的拿着扑克牌在发牌,有的捧着拖盘来回踱步。
离我最近的阿修站在面前背对着我,他的前面摆着一张泊车台,他的手从背后朝我伸来,比划出了一个“来“的姿势,我把手伸向他,站了起来,然后我们一起走到天台边缘,他单手张开挡住了我,不让我再前进,我向外看去,大楼已经变成了一座一座的灯塔,泊油上都是热浪。阿修撑起手坐在围墙上俯看着我,其他阿修都不见了,这座孤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阿修说“已经没事了。“ 可是怎么会没事,我甩着头,从今往后我都得一个人在那种地方活着,不会有人拿着热呼呼的毛巾到我下台的包厢门口扔给我,不会有人关心我被哪个客人咸猪手,又被哪个干部斥责了,不会有人在我上班的门口拿给我一罐鸡精,下班的时候再递上柠檬水,不会再有人说要保护我了。
而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整件事情都是我害的。
阿修摇头对着我苦笑,一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死了,把满满的负罪感留在我往后的生活里。 “有些人他本来就应该要死去。“阿修又说。
他从围墙上跳下来,没有再靠近我,他往门口的方向走去。我抬起头,岛上只剩下我自己,从此以后。
那天轮到阿修站在泊车台,下班前那桌我吃了两颗药还有一些K粉,结果那桌只坐了不到三个小时,药效都没有退就下台了,离开包厢前客人把剩下的药丸分给了在场的小姐,我也被分到一颗。
如果是我清醒的时候,我是不会那么做的,我不会把那颗药丸拿给阿修,我可能会拿给有在用药的小姐,或是丢到垃圾桶,可是我当天浑浑噩噩,又急着想要跟他有什么互动,药丸就这样落到了他手中。 那颗药便成了他几个小时后的“幸运药丸“。
后来我没有再吃过药,我让阿修彻底的从我的生活中离开了,留下来的都是愧疚。休息一个礼拜后我继续回到那所地狱折磨自己,即便阿修不再站在泊车台,即便他不再进包厢送毛巾和酒,可是他还是在我心里无限穿梭着,一直到下个轮回,也许可以换我保护他,不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