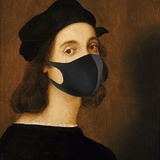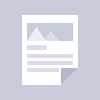走出客运站,拐进一个巷子,过几排房屋,便能听到阵阵哀乐,我就知道是大伯家到了。叔伯婶娘都在那里,父亲母亲也在,大家忙乱地准备吊唁用的各项事宜。我穿过人群,找到正在照看侄子们的母亲,她接过我的背包,让我把手上的拉杆箱立在墙边。父亲也过来了,他捏着我的手,说:“冷啵?”见我摇头,又说,“跟你大伯见见。”大门口的小桌子上供放着大娘的遗像,后头是黑沉沉的棺材,我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她已经火化了。走进门去,大伯的两个儿子,我的大堂哥和小堂哥,已经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跟叔爷谈论明天回乡下安葬的事情。大伯坐在堂屋中央的小板凳上,被一圈人围着,我过去叫了一声,“大伯。”大伯颤巍巍地起来,握住我的手,眼眶红红,满是泪水,“你回来了?……我是一夜都没有合上眼,你大娘走得实在太急了……”我一时间呆立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安慰的话也说不出口,还好母亲过来叫我去吃饭。
大娘的离世,所有的人都很意外。想起过年时来大伯家拜年,他们家大门紧锁,我只好在外面等。不一会儿,我便看到了他们。远远地,大娘拎着两大袋菜,健步如飞地往我这边走;而大伯慢腾腾病恹恹地跟在后面。我那时候心想:“大娘看起来真是有精神气!大伯可能熬不过几年了。”大伯一直以来都被糖尿病所苦,年纪越大,身体越发孱弱下去,眼睛视力也变差了,得亏大娘的精心照料,他才得以生活得体体面面。大娘个子高高,说话声音洪亮有力,以前是教师,我好几位叔爷都是她学生。大伯过去在部队里是连长,退伍后转到事业单位做领导。两人退休后,都有退休工资,不需要靠儿子们来养,对靠在田地里谋生活的我父母这一辈人来说,可以说最值得羡慕的两口子了。
大娘离世的那一天,没有任何异常。大堂哥和小堂哥两家都出门了,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大伯住在一楼,他起来洗漱完,忙了一会儿,一看时间八点半了,大娘还没有从她睡的四楼下来,按往常来讲,她每天七点多就已经下来弄早餐了。大伯站在楼下喊大娘的名字,没人答应,他便上楼,一边上一边喊,还是无人答应,他心里渐渐有点儿恐慌起来,到了四楼,他又喊了几声,只有自己的回音,他心里往下一沉,知道出事情了。他推开房门,大娘躺在床上,被子还是晚上睡觉时那样,因为天气冷所以裹得紧紧的,看起来一点儿没动,大娘的嘴巴张大,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了任何生命体征。大伯站在那里,掀开被子,对着大娘说:“你就这样走了啊?!就丢我一个人了?”
大伯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又一次哽咽起来。父亲陪着他坐在堂屋,大娘的姐妹来了,乡下的众多亲友也都来了。 湿冷的风一阵阵吹进门,大家都把手捂在口袋里。父亲时不时站起来,跟堂哥说起吊唁要用的各种物件,嗓子都哑了。是他第一个赶过来陪着大伯的,还打电话叫大堂哥和小堂哥赶紧回来——他们那时还在上班的路上。对堂哥们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父亲指挥堂哥们把大娘从四楼背到一楼。已经冷却的身体非常沉,小堂哥背得特别费劲,好不容易搬到了堂屋,他已经是满身汗了。大娘的手和脚都是硬的,赶回来的堂嫂们给她穿衣服,弄了半天都很难穿上……因为去世得太过匆忙,从哪里买棺材,如何准备寿衣,怎么联系道士,都是一团乱麻,得亏有我父亲和叔爷们帮衬,才一一搞定。
大娘去世的消息,迅速地在我们的家族微信群里传开,我赶紧买回来的火车票,同时间我哥哥,还有其他堂哥堂弟堂姐们,都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在母亲叫我出去吃饭的当儿,陆陆续续地,我二父家的两个堂弟都来了,姑姑家的表哥也来了。大家其实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碰面,现在没想到在这个场合下又一次重聚,却没有多少话可以讲。他们的孩子坐在他们身旁,我没有一个能叫得上名字。大家吃着喝着,请来的乐队吹着打着,一时间分不清是丧事还是喜事。那一刻我觉得有这些仪式挺好的,唯有这些喧嚣和忙乱把人裹在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里,不至于骤然直面亲人离世之痛。但一旦丧事结束呢?漫长的未来都是亲人的离席,那种缓慢的痛苦只能每个人独自承受了。
棺材明天早上要运回乡下邓垸祖坟处安葬,大家吃完喝完,都准备回乡下了,没回去的在堂屋架上麻将桌打牌,毕竟守灵是漫长而无聊的。我们坐上了胖爷运灰的小卡车。后车厢没有任何遮挡,我把行李箱放倒,让母亲和细姑坐在上面,而我自己跟两位叔爷抓住栏杆。车子上了长江大堤,江风浩荡,吹得人全身冷透。刚过十五,巨大的圆月悬挂在防护林的上空。透过疏阔的林地,暗黑的江水流淌,对岸有零星的灯光。母亲和细姑缩着脖子靠在一起,说起大娘是个有福气的人,“连死都是这么好,没有么子痛苦就过去了,可以说最理想的死法了。”而两位叔爷讨论明天棺材该怎么送到坟地,“如果从坝上走,直接用车子开过去,倒是很方便;如果从垸里穿,热闹些。葬礼还是要热闹点儿好。”我的手已经冻僵了,母亲让我把手塞进她大衣口里捂着。隔着衣服,能感觉母亲身体的温热。她还在跟细姑聊天,一说话,身体震动,我的手也能感觉得到。
回到家,洗漱完,陪母亲看了一会儿电视。父亲还在城里,明天侄子们还要起来上学,他得照应着。因为两个侄子都在市区上学,为了能照看方便,哥哥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母亲因为舍不得家里的地,偶尔来住,倒是父亲非常喜欢在那里。每天送孙子们去上学后,他就可以去龙潭公园玩,时常在那里碰到前来散步的大伯,两兄弟一辈子都没有这么长时间坐在一起晒太阳。大伯家也是走几步路就到了,父亲没事也会去他家坐着聊天。父亲事后一再跟人说:“我大嫂从来就没有靠着我坐那么近的说话,那天说了一下午。么人晓得第二天就没了呢!”现在父亲可能还陪在大伯身边吧。
电视台上反反复复放着的都是抗日剧,打扮时髦的打鬼子英雄,一排人对着打都打不准,看得我心生倦意,但母亲却看得津津有味。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母亲忽然感叹,“家里多个人还是热闹。我一个人在家里很早就睡了。”说起父亲,她摇摇头,“他哦,几快活的!天天跟城里的退休老头儿一样,去公园打打牌,早餐还去买的吃。”我说:“这个没得么子,买个早餐也没几个钱嘛。”母亲一拍手,“早餐一吃四五块,一个月下来不得了哦。一年下来重花多少钱!”我笑了,“钱不用担心嘛,有我们。”母亲摇摇头,“你们挣钱也辛苦。”想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之所以还要种地,还是想多挣点钱,至少我跟你爷的吃喝花费都有了。我不想麻烦你们。”
到该睡觉的时间了,母亲给我铺好了床,准备好了被子。我钻进被窝,母亲问:“北京是不是很冷?”我说:“有暖气。”她点点头,又问:“被子薄不薄?要不要再加一床?”我说:“不用了。”她说好,转身走开,走到门口,又说:“早点儿睡,莫又看书看到很晚。”我“嗯”地一声。关了灯,清冽的月光洒了进来。我得抓紧时间睡觉:明天六点就得起来,母亲要跟二娘熬粥,准备好饭食,明天来吊唁的人会很多;而我要赶到城里大伯家里,参加诸多吊唁仪式。我忽然想起小堂哥背着自己母亲的尸体下楼时,会是什么心情。前一天生活一如往常,上班是上班,上学是上学,打牌是打牌,做饭是做饭,一夜过后,忽然所有的事情都崩塌了。母亲没有了,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连一句话都没有,连我这样的外人想起来都是痛的。再想想大娘,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那是她的最后一夜,她死的时刻真的毫无痛苦吗?这个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我跟大娘几乎没说什么话,也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心里的难过还是升腾起来。楼下,母亲走路的声音,开灯的声音,关门的声音,一一响起,又一一消失。周遭安静了下来,只有风撞着玻璃窗,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