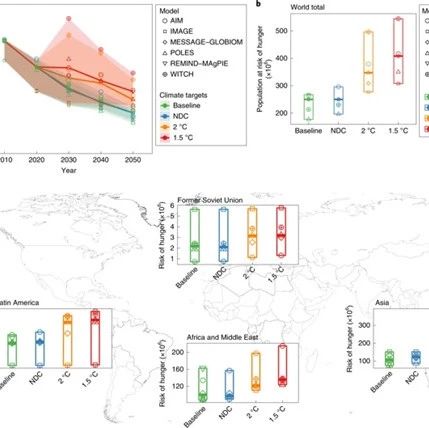3 永远都不要逾越不该逾越的鸿沟
在读完《刺杀骑士团长》的第三章之后,高桥小姐轻声提醒我说,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我看了下手表,才发现距我们约定好的每次两小时还差三分钟。
“还有五分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故意多说两分钟,也许那个两个小时后就可以脱身而出的真实的“我”想跟高桥小姐再说会儿话,不是以“陈君”的身份,而是以那个谁也不知道的真实姓氏与她交谈。
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与纠纷,公司规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用自己真实姓名。所以与客户见面时,我一直都在用各种各样的假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我可以替自己取任何名字,然后在渐渐厌倦那个自己塑造出来的形象之后,摇身一变,像细胞分裂一般,再分裂出一个全新的身份。公司会根据员工的要求,制作相应必要的身份证明,像名片、证件之类的(当然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可也不能过于频繁地更换,只有在接手新客户,或者当之前的名字对私生活产生无法解决的困扰时,才可以向公司申请使用新的名字,当然,在更名前仍未终结的契约关系中,仍须使用之前的姓名。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公司规定每个员工同时保持的契约关系最多为五条,所以一个人最多可以有五种不同的姓名和身份——严格来说,加上最原本的那个自己,是六种。有些员工会觉得名字换来换去十分麻烦,所以至始至终都用着同一个假名,这样倒也省了不少事,只要将自己活成两种人便可,像公司里元老级的员工中岛先生,听说他从进公司起就一直在用中岛这个姓氏,已近四十年。还有与我大抵同一时间进公司的川村小姐,她工作时也从未换过名字,她说那些会提出各种稀奇古怪要求的客户已经让她忙得够呛了,哪还有闲情雅致去想破脑袋琢磨出另一个名字来。
然而我却热衷于使用不同的名字示人,就像我之前写小说一般,我总喜欢用第一人称来写,可以替在不同的小说里无数次出现的那个“我”取任何乐意的名字,配给“我”们形形色色的性格,“我”可以是个作家,也可以是杀人犯。这常常让我暗暗窃喜,仿佛比其他人多出许多种人生来一般,被束缚在肉身里的那个“我”可以像拉面团一样被无限地拉伸,再拉伸。
所以我会在看完客户资料里所有的要求,确定接手这个契约关系之后,就会替自己取一个尽量与之相匹配的名字。在确定接手奥田京子这个客户之后,我在和川村小姐一起去喝咖啡,拿出记事本,向她展示了自己新名字,川村小姐一如既往地对我的新名字露出了鄙夷之色,她一边嘬着咖啡,将视线暂时从手机屏幕上离开,慢悠悠地斜视我一眼,扯动一下嘴角,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声音,然后继续看向手机屏幕,轻声念了一遍我的新名字之后说道:“我可看不出,你这个名字里的哪一笔可以证明你会是一个温暖的父亲。”
“那你是不懂中文的博大精深。”我也斜了她一眼,川村小姐是与我关系最好的员工,私下里也成了我为数不多的日本朋友,没事时会经常一起出去喝酒吃饭聊天。只不过这个朋友的特殊之处就在,我一直都不知道她真实的名字,就像她也不知道我的一样。对我来说,她是一个暂且用“川村”来称呼自己的女子;对她来说,我今天是陈,明天是董,后天是赵,再见面又变回了陈……我们曾一起接受公司的新员工培训,还在实习期扮演过一星期的恋人,同吃同住,只不过睡的是两床被子。
“要我说啊,名字啊,衣服啊,甚至是我们的身体啊,这些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剥去这一层层的外壳之后,里面的那颗核的形状、颜色和温度。可懂?”川村小姐故作深沉道。
“既然这些都不重要,那你告诉我你真实的名字吧。”我虽然开玩笑似的说着,但我是真的想知道她的真名。
川村小姐也嗤嗤地笑了,竖起食指在我面前摇了摇:“我还以为你要我在你面前脱光衣服给你看的呢。陈君——现在坐在我旁边的你是姓陈吧?”
我点了点头。
“陈君,要记住,永远都不要逾越不该逾越的鸿沟哦,会葬身沟底的,会被埋得跟淤泥里的莲藕一般死死的。”
我冷笑道:“你这身材,不用脱我也知道,半点看头也没有。”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我在睁眼说瞎话,川村小姐的身材其实很有看头,个子不算高,但前凸后翘,四肢修长,侧脸的轮廓棱角分明,或许家族里有一点西方血统。
川村小姐抬起手作势向我打来,我一躲,她打翻了桌上的咖啡杯,哇哇地叫着跳了起来……
其实我也知道,名字什么的,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但我还是会乐此不疲地更换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了解自己的性格,每一个角色我都只能浅尝辄止,我有我自己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怕自己会陷在某一个角色里难以自拔,像“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永远都被束缚在虞姬的那套装扮里,戴着千斤重的点翠头面,鼓点锣声里的每一寸挪步,都是在抻着脖颈,慢慢靠近霸王麾下那泛着冷光的剑口。
“还有五分钟。”高桥小姐像是在自言自语般重复了我的话。
“你是怎么知道时间快到了的?你又看不……”话没说完,我就发觉自己失了态,立即收住了口。
在听我读完小说之后,高桥小姐的心情似乎变好了许多,完全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眼睛继续“盯着”面前书架上的某一个角落,轻声问我道:“你是不是想问我的眼睛又看不到,是怎么确定时间的流逝的?”
我点了点头,又意识到高桥小姐无法接收到点头这个动作,于是又轻声“嗯”了一声。
高桥小姐微微笑了下,说道:“你在这个 ‘嗯’之前,是不是点了头?”
我惊讶的看着她:“你怎么知道的?”
“虽说失明给了我致命的打击,但在我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再静下心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世界,我发现周围的一切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什么都变了。周围还是那个生活了二十几年的世界,可感觉到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看不见的东西或者说被我的双眼自动过滤掉的东西,现在我都可以清楚地 ‘看’到了。我可以看到风的形状,阳光的色泽,雨水的气味。我也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呼吸来判断他的心情,通过他的声音来判断他的性格。就像刚才,我从你脖颈摩擦衣领的声响,判断出你应该是点了头。”
我低下头确认自己脖颈与衣领接触时是否发出了什么声响,的确有微乎其微的摩擦声,但这犹如草丛中有昆虫爬过的轻微声响她居然都可以听到。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连时间这无形无色的概念都似乎跟测量尺一样,有了具体的形状,我的脑海里有一轮巨大的挂钟在一刻不停地转动着,只要我每天起床后跟母亲确认过一次时间之后,接下来这一天的时刻我基本都可以相差无几地估计出来。”
“像是学会了一种绝世神功。”我开玩笑道。
“我不知道其他的盲人是怎样,但我的确是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这个技能,对于你们明眼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这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我感知外界世界、与外界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
我想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但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成日语说给高桥小姐听,只好开口道:“这就是所谓的 ‘有失必有得’吧。”
高桥小姐又笑了笑,调整了下坐姿,充满笑意的目光又落在了我的脸上。她的双眼十分纯净,泛着水光,有那么一瞬间,我一厢情愿地幻想高桥小姐可以看得见,我喜欢她这种含情脉脉般的注视。
“陈君,下次见面我们不读书了,帮我做另一件事可以么?”
“如果不超过摸脸这个限度的话。”我笑道。
“你的脸我已经了然于心了。”
“我的脸就悬在挂钟的旁边?”
“就在钟盘里,鼻尖上钉着两根指针。”高桥小姐笑颜如花。
“像17年迪士尼电影《美女与野兽》里的那个时钟人?”我随口问道。
高桥小姐略微停顿了一下,收起脸上的笑容,略带失落地说道:“失明后我就再也没去电影院看过电影了。时钟人什么的,也只能靠自己想象了。”
我摸了摸头,暗骂自己就是个蠢货,沉默了片刻后转口问道:“那你说说看,我们下次见面时做什么?”
高桥小姐说道:“要是我的感觉没错的话,五分钟应该已经到了。”
我看了眼手表,果然下午五点两分刚刚过去十几秒,果然厉害。
高桥小姐笑了:“现在,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就让我留个悬念好了,下次见了面再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
“又不是侦探小说,留什么悬念?”
“这样才会有期待不是,有期待的人生总要快活一点的,这是我近来的感悟。”
“说的也是。那我拭目以待。”
收拾好东西后,高桥小姐又牵着我的臂弯,拉开手中的盲人拐杖,像进来时一样跟在我后面,缓缓地走出书店,向下走完两段式的二十四层台阶,穿过海水下四处飘摇的水草般四处奔走的人群,走进地铁站,乘坐最近的一趟列车回家。
我将高桥小姐送到电车站台后,在她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示意她已经到了站台。
高桥小姐略一踌躇,然后从我的臂弯里抽出手,双手在拐杖上紧紧地握成一座山峰,转过身来面向我,然后突然想起什么似得在挎包里翻了起来,接着拿出一个棕色信封,摸索着交到我的手里。
“差点就给忘了,今天承蒙照顾,我过得十分开心。”高桥小姐对我笑着说。
我脑海里浮现出她在摸我的脸时无声哭泣的样子,几欲问出口她为什么哭,可外衣上一直拉到领口的拉链似乎连喉咙也一起拉上了,一个音节也问不出口。
我摸了摸手中的信封,心头莫名地多了点惆怅,可下一秒又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你的工作,这是你自己选择戴上的假面,这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契约关系。我将信封放进包里,与奥田京子之前给我的那个信封放在了一起,然后抬起头,笑着对高桥小姐道了谢。
高桥小姐在我面前低下头去,似乎在酝酿着什么话,刚抬起头对我说出一个:“那个……”,鸣着刺耳笛声的列车就从黑暗的轨道里扭了个身,呼啸而来,带来一股洪流般的地下强风。我下意识地将高桥小姐往前拉了一把,随即松开了手,问她刚才想说什么。
渐渐停稳的列车在高桥小姐身后打开了车门,车上的人鱼贯而出,站台上的人鱼贯而入,高桥小姐只是笑了笑,说也没什么,然后跟我道了别,转过身去,摸索到车门,用拐杖试探列车与站台间的空隙,然后一脚跨进车厢里去,抓住车门旁的不锈钢扶手后,转过身来朝我的方向挥了挥手。
车门口的警示灯开始闪烁,车门将在三秒后关闭。看着车厢内拥挤人群里瘦小的高桥小姐,我突然很想跳上车去,将她一直送到家中。可看到列车与站台间那条间隙时,我想起了川村之前跟我说的那句:“要记住,永远都不要逾越不该逾越的鸿沟哦”,又缩回了脚。
列车车门像两片凛冽的刀口一般慢慢闭合,站台上的列车员吹响哨子,与列车司机互相打着手势,确认安全信息,列车司机拉下操作杆,列车开始缓缓蠕动起庞大的身子。
我也朝着渐渐离去的高桥小姐挥了挥手,因为知道她看不见,我才敢抬起了手。可谁又敢肯定,高桥小姐就真的感受不到我在挥手呢?毕竟连时间都是站在她那边的。
我看着现在已经犹如蛟龙般飞速离去的列车在轨道尽头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又回过头来看着从我身旁走过去的一幅幅陌生的面孔,突然有点不知所措。今天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可我又不愿现在就回到那间单身公寓里去,与冰箱的嗡嗡声,水龙头的漏水声为伴。可现在一时我又找不到可以去的地方,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只要想见就可以见到的朋友。
就在这时,川村小姐打来了一个救命般的电话,问我在哪,是否有时间一起吃个饭。
我在说出一连串的“有有有”之后,怅然意识到,在这春日黄昏的暮霭中,这世上像我一般无所适从的人大有人在。
电话那头的川村小姐似乎刚睡醒的样子,打了个哈欠,轻描淡写地对我说道:“正好见面和你说说有关明天婚礼的事情。”
我这才记起,我明天还有一场婚礼要参加——不是作为宾客,而是作为新郎。没错,明天又是一场盛大的演出,新的假面要被换上,明天的我会有一个如新郎般美好的名字,也会有一个美丽的新娘在等着我喜结连理,然后在亲朋好友离去后,礼貌地互相道谢,分别——就算下次在马路上撞见,也会装作互不相识,匆匆离开。
川村小姐的声音渐渐远去,我不禁屈起手指,暗暗计算:这是我人生的第几次婚礼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