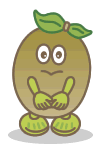文/郑宪
沪闵路,当年大名鼎鼎的中国机电工业4个万人大厂就在这里周围,路两边景色为美丽的乡村形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美妙结合。如今,现代城市所拥有的繁华元素和景观,已将原来路两边乡村的美丽符号荡然抹平,但是我们飞扬的青春和肆意的欢笑,依然在眼前飘过,在耳边回荡。
40多年前,在沪闵路上,年轻的我们,做过一件锻炼体魄心志的事:用脚丈量20多公里柏油路,起始西渡口,止于徐家汇。我携一水壶,走到脚底布上血泡,小腿肚子抽筋,时间是一个上午加半个下午,最后在苦痛的坚持中望见徐家汇尖顶教堂。
今日驱车重走沪闵路,农田稻浪已不见,油菜花了无踪影,成林的桃花不再摇曳,拖拉机行驶的机耕道无处寻觅。
沪闵路是我们的骄傲
40多年前,来回四车道的沪闵路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笔直延伸,开阔平坦,路边15米一间隔的亭亭香樟,如受阅的士兵整齐排列。沪闵路两边,一片片规整农田,大河小湖,是农人劳作舞台。春天闻香甜,秋天见果实,收割的男女农民,朴实而沉醉的脸。
有人说,当年建此路,与建老闵行工业重镇一样受重视:重要领导亲临督阵,苏联专家共同设计参与,才有这条超前之路。
上左为今日上海重型机器厂,上右为上海电机厂,下为上海汽轮机厂
那年,我在老闵行学徒工满师,想买辆自行车,在沪闵路上骑驰。其时父母负担重,日子紧巴,家里已有一辆车,父亲在骑。结果父亲无奈退让:你骑,我上下班走路。我听之,竟心中窃喜(恕我少不更事)。那天起,我便骑上父亲七成新的自行车,从徐家汇到老闵行工厂,春风得意马蹄疾:沪闵路,我来了。
曾经,到老闵行是骄傲,走沪闵路也骄傲。
那时的沪闵路,除壮阔美丽,又是一条灰尘漫天充满噪音的路,大小拖拉机横冲直撞。只是当年浑然不觉,倒是认为,一切缘于勃勃生气,连撞鼻而来的汽油柴油味也香气提神。
人单纯又知足,幸福来敲门。一周最后的工作日,下午一点钟下班,车间主任说:“最后两炉锻铁,并一炉锤打:放个小高产,打击帝修反;早放半小时,骑车返上海。”痛快的动员令,让我们及时完成任务。一点前,我们锻工车间几十辆新旧自行车,早一字排列候在厂门口。时间到,厂门开,车铃响云霄,捷足快蹬,汹涌而出。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闵行的年轻锻工
突突突的拖拉机,是当年沪闵路上一道风景。有小型手扶拖拉机,也有带正式驾驶座位的大中型拖拉机,从一条条乡间机耕道驶入沪闵路,嘶吼着,冒着滚滚黑烟黄烟,驶过你跟前,湮灭你的说话声。不反感,非但不反感,还去“拥抱它”:跟上,猛骑,再果断伸出一手臂,手指手掌迅疾握住拖拉机后车身的边缘一角,便搭上了贫下中农的顺风车。如此,腿脚不用骑蹬,车已加速往前。这行为,危险,但节省体力,爽。
那日,青工周国辉和平时一样,拍马前行,手搭上一台拖拉机,众将左右呼拥。殊不料,开拖拉机的贫下中农愣头青不愿意,急加速,还开起S形,意在甩脱搭车人。兀地出现一块大石砖,横亘在国辉自行车前轮,想避不及,自行车瞬间哐啷倾倒,人被甩下车。甩下的人,手肘手背皮伤不说,后面驶来一辆汽车,贴着倒地的国辉头皮几厘米远,呼啦碾过去......
所有周围骑手吓得脸变色。贫下中农急停车。一群年轻工人红紫脸围上去。要干架?没有,愣头青贫下中农也吓傻了,向工人阶级嗫嚅道歉,要送受伤的国辉去乡里卫生院。
惊吓只在半分钟,国辉已从地上骨碌爬起,拍拍满是灰尘的头发,将自行车扶起,车龙头扳正,再拍一下愣头青贫下中农的头,“记牢,工人和贫下中农是兄弟。以后要兄弟帮兄弟。懂了伐?”遂翻身上车,又手搭上另一台拖拉机。所有人,风一般跟上。
这故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沪闵路上,在我们骄傲的小青工嘴里,成为“传说”。
骑行在沪闵路上的女工
穿过40多年光阴,依然记得沪闵路上徐闵线公交车的站牌点:徐家汇—漕宝路—西牌楼—梅陇—莘光小学—莘庄—春申桥—徐家湾桥—颛桥—精神病医院—北桥—畜牧场—剑川路—招呼站—轴承厂—一号路—西渡终点站。西牌楼在今天铁路南站位置;而当年荒郊的莘庄,是此路的“南北分界线”;骑过外墙暗红色的精神病医院,心想有没有女精神病人透过密密的铁窗在张望我们;过招呼站,是提醒骑车人,目的地将临,现代化工厂天地要到了。
今天的沪闵路
今天造访沪闵路,观望许多空调大巴车串起的徐闵线,细看新站牌,有删减,有替换,有新加。新加的路,都是金银满地喜气的名:报春路,银都路,金都路,贵都路,金塔路,鹤庆路。这些路的左右,万丈起高楼,想原来,这里都是稻谷满地香,桃李满天下。
历史留下了沪闵路,照单全收地保留了它的长短宽窄,但路两边,不见初始的景致。
忽然想起个人:杨妙贞。杨是沪闵路上的骑车女王。当年的一出《红色娘子军》受到我们尊崇,杨在工厂,也受到“娘子军”般尊崇。为什么?因为她和最强劲的男子一样,将沪闵路十几年征服在骑踏的脚下。甚至,许多男人也不能跟她比速度。
当年有句话:“苦不苦,想想妙贞的咸菜肉丝淡馒头。”此话怎讲?杨家住闸北西宝兴路上,10个平方米居10口人,大弟在部队因公牺牲,丈夫工作在遥远外地。家中她老大,60元的工资要承担三代人生活。她一月留给自己的生活费是多少?6元。杨骑行沪闵路的原因就两个字:节约。她极度珍惜那辆26英寸凤凰自行车,是厂里允许她分期付款而得到的,一月10元,12个月付清。她要让这辆自行车“生出钱”。
骑自行车,一个月省下来的公交车费用,近6块钱。
每周她在厂里吃的菜,是骑车从家里带来的一大瓶咸菜肉丝,就着食堂里的免费汤,顿顿吃得香,有人遂叫她:“咸菜肉丝”,她快乐应之,咸菜肉丝便成为她另一个名字。
厂里兄弟姐妹一起加班,加班的奖励是一张淡馒头的券。便有人说:杨家一帮兄弟胃口大,券省下来给她。杨妙贞啥东西都不要人家的,唯有这淡馒头券,她感激不尽地收下。到周末最后一餐,集中买进,骑车带回家,“沪闵路上我骑得飞快,一路风景越看越好看。想厂里兄弟姐妹一片情,家里人马上都能吃到白胖的淡馒头,开心唻。”
时至今日,我将当年有人说的话告诉85岁的杨妙贞:娶妻当娶杨妙贞。她竟黑色幽默了一下:“瞎讲有啥讲头,沪闵路听到也会笑出声。”
当年沪闵路上骑车女王杨妙珍,今年已经85岁了,精神矍铄
沪闵路上不会再有杨妙贞那样的人了。
他们是不可少的螺丝钉
王美珍说:“我一家,大半的人都在电机厂里打磨成器。”
上海电机厂一号正门就在当年闵行一号路(现在叫江川路)上,曾经的号码:一号路555号。她父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带着母亲,从川沙乡下出来,靠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走进电机厂的门,就此深深扎根,做冷作工,一做做到七级半工,当年评工资,105元,“自己也吓了一跳”———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父母育六个子女,王美珍老幺。前面几个,大哥当了兵,回来入了电机厂,二哥随即读书考进。还有一个小姐姐,最后顶替父亲,也一头扎进了这工厂,开大车间头顶上来来往往的大行车。
上海电机厂内的厂内铁轨
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普通人不会受很多诱惑,选择一个地方,认准有个好发展,铆着劲干活就是。老闵行,电机厂,大门口每天几万人汹涌吞吐,他们就是隐没在其中的几颗小螺丝钉。但螺丝钉有自己生存的意志、毅力和快乐。
家里发生这样一件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母亲的一场大病和在病痛面前的不屈抗争,且和沪闵路相关。
都说母亲活不长。但父亲对母亲说:“厂里管我,我要管好你。你心宽,就能活回来。不怕,我带你去看病。”那是怎样的坚持,除了工厂上班加班的日日辛劳,周末,父亲骑辆自行车,车架后面驮着母亲,风里雨里日头里,骑在沪闵路上,一次骑行几十公里,往莘庄,往上海(那时对从郊区到市区的说法),再一脚脚骑回老闵行,往返一次5个多小时。也算一次次“长征”。
母亲有退缩,几番打退堂鼓:为治病,买各种贵重药,原来收入宽裕的家庭难撑持。父亲说,我有力气,家里孩子等着你。“你看笔直直的沪闵路,一路没障碍,我们就要给孩子立榜样:不泄气。”
骑了整8年。终于,这病魔终被驱赶殆尽。一对恩爱夫妻扶持到老,母亲活了八十二,父亲寿享八十七。
王美珍讲的,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家的家风。父亲说自己缺文化,那就老老实实在厂里只干活少说话;母亲身体不好,那就负责养好身体顾好家。家里最早的房子,是工厂分配在一号路边十几平方米的屋,三代七口,睡觉全是双人铺,酷热寒冷共担。现在回想,兄弟姐妹的感情那时处得最浓。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改善住房,分到27.2平方米的居室,全家欢腾,感觉已生活在天堂。
王美珍说自己已是老闵行的“原住民”了:生于兹,长于兹,学习于兹,工作于兹。守着老闵行,守着已变成江川路的一号路,心平气和地生活。
我对王美珍说,40多年前,我们工作在工厂,骑行在沪闵路,生活在一号路,有赳赳之气。想到当年两句话:到了上海不到闵行,等于没到上海;到闵行不去看“四大金刚”(四个万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白走一趟。
王美珍笑起来,说现在她常去市中心,乘车过沪闵路,时常想:父亲早年用自行车骑着病弱的母亲,一脚一脚吃力伐?父亲母亲,这样的坚持和努力,想想,也很伟大。
沪闵路上唱歌的农家娃
严平和我们有十多年友情,却在近日,无意中说到一个共同话题:沪闵路。他说,我就是沪闵路边长大的农家娃。
我对他说:40多年前,在沪闵路上,我们工厂小青工,来回在市区、老闵行间骑自行车,和你父亲后座驮着年幼的你的自行车,或许哪一天,是交叉而过的。他说:很可能啊。
今年50多岁的严平讲起40多年前,他在沪闵路上看见那些“上海小青工”时的憧憬:他们经常穿着工厂的劳防服装,骑着自行车,也有乘在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厂车里。他一个乡下的小学生,羡慕嫉妒恨也来不及。他的出生地:颛桥乡友谊大队第六生产队,父亲则是中学教书匠。小学去莘庄读书,走路要两小时。走就走沪闵路,也乘徐闵线公交车。上了徐闵线,小孩时身子往下蹲一蹲,不到买票“身高线”,可以省下一角五分钱。后来人长高,那就多走一站路,少乘一站车,省下五分钱。走路时要走过那个精神病医院,害怕精神病人忽然冲出来,就唱当年的一首首歌,给自己壮胆:“打蛇打七寸,斩草要除根,批林批孔齐上阵,革命向前进”。也唱:“小松鼠,快长大,绿树叶,发新芽……”
上世纪七十年代沪闵路边的农家娃严平(右一),后面是他的父亲
以往,沪闵路上可以看到农民在三夏、三秋、双抢。有时我们工厂小青工也会在农忙时呼啦出动,帮贫下中农兄弟一把,和贫下中农“三结合”。但我只去过奉贤,靠近南桥。沪闵路上,对贫下中农劳作的身影只是遥望。
严平是看着沪闵路的变化长大起来的。记忆中的学校暑期,也要忙农活,到队里饲养场烧茶水,茶水里放决明子和大麦。烧了水,嘿呦嘿呦送田头。这劳动也算工分,一个工,三角三分钱,和大人一个工一块钱有区别。快乐的时光是随哥哥到河浜边抓蟛蜞,回来煮个蟛蜞烧老黄瓜。调皮的事情也发生过,到沪闵路旁边,偷吃别人家未熟的桃子、甜芦粟,挖人家的山芋,摘别人家的西瓜,被发现,被告状,然后,“吃一顿生活”。
那时候我们工厂中班下班,骑车回上海,晚上八点出老闵行厂门,回上海的家,要夜里十点多。一路沪闵路,除夜行的拖拉机突突驶过,黑灯瞎火,但闻声声狗吠。严平听了笑起来:那时的乡下头,尤其在夜里,给你三句话,通话靠喊,交通靠走,治安靠狗。
往事可回味:在沪闵路边一处水稻地里,严平曾举着一长棒,衔一长线,去吊水中的青蛙。有架轰隆隆的飞机头顶飞过。他便想:我这个“农家娃”,这辈子会乘上飞机吗?
而今,他这个研究生毕业好些年的国家干部,一次次去国外考察,再回到沪闵路边的家。
回味回不去的往昔。好在,巨变后的今日,也自有一味别样的芬芳———去看看香樟葳蕤的沪闵路吧。文/郑宪
沪闵路,当年大名鼎鼎的中国机电工业4个万人大厂就在这里周围,路两边景色为美丽的乡村形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美妙结合。如今,现代城市所拥有的繁华元素和景观,已将原来路两边乡村的美丽符号荡然抹平,但是我们飞扬的青春和肆意的欢笑,依然在眼前飘过,在耳边回荡。
40多年前,在沪闵路上,年轻的我们,做过一件锻炼体魄心志的事:用脚丈量20多公里柏油路,起始西渡口,止于徐家汇。我携一水壶,走到脚底布上血泡,小腿肚子抽筋,时间是一个上午加半个下午,最后在苦痛的坚持中望见徐家汇尖顶教堂。
今日驱车重走沪闵路,农田稻浪已不见,油菜花了无踪影,成林的桃花不再摇曳,拖拉机行驶的机耕道无处寻觅。
沪闵路是我们的骄傲
40多年前,来回四车道的沪闵路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笔直延伸,开阔平坦,路边15米一间隔的亭亭香樟,如受阅的士兵整齐排列。沪闵路两边,一片片规整农田,大河小湖,是农人劳作舞台。春天闻香甜,秋天见果实,收割的男女农民,朴实而沉醉的脸。
有人说,当年建此路,与建老闵行工业重镇一样受重视:重要领导亲临督阵,苏联专家共同设计参与,才有这条超前之路。
上左为今日上海重型机器厂,上右为上海电机厂,下为上海汽轮机厂
那年,我在老闵行学徒工满师,想买辆自行车,在沪闵路上骑驰。其时父母负担重,日子紧巴,家里已有一辆车,父亲在骑。结果父亲无奈退让:你骑,我上下班走路。我听之,竟心中窃喜(恕我少不更事)。那天起,我便骑上父亲七成新的自行车,从徐家汇到老闵行工厂,春风得意马蹄疾:沪闵路,我来了。
曾经,到老闵行是骄傲,走沪闵路也骄傲。
那时的沪闵路,除壮阔美丽,又是一条灰尘漫天充满噪音的路,大小拖拉机横冲直撞。只是当年浑然不觉,倒是认为,一切缘于勃勃生气,连撞鼻而来的汽油柴油味也香气提神。
人单纯又知足,幸福来敲门。一周最后的工作日,下午一点钟下班,车间主任说:“最后两炉锻铁,并一炉锤打:放个小高产,打击帝修反;早放半小时,骑车返上海。”痛快的动员令,让我们及时完成任务。一点前,我们锻工车间几十辆新旧自行车,早一字排列候在厂门口。时间到,厂门开,车铃响云霄,捷足快蹬,汹涌而出。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闵行的年轻锻工
突突突的拖拉机,是当年沪闵路上一道风景。有小型手扶拖拉机,也有带正式驾驶座位的大中型拖拉机,从一条条乡间机耕道驶入沪闵路,嘶吼着,冒着滚滚黑烟黄烟,驶过你跟前,湮灭你的说话声。不反感,非但不反感,还去“拥抱它”:跟上,猛骑,再果断伸出一手臂,手指手掌迅疾握住拖拉机后车身的边缘一角,便搭上了贫下中农的顺风车。如此,腿脚不用骑蹬,车已加速往前。这行为,危险,但节省体力,爽。
那日,青工周国辉和平时一样,拍马前行,手搭上一台拖拉机,众将左右呼拥。殊不料,开拖拉机的贫下中农愣头青不愿意,急加速,还开起S形,意在甩脱搭车人。兀地出现一块大石砖,横亘在国辉自行车前轮,想避不及,自行车瞬间哐啷倾倒,人被甩下车。甩下的人,手肘手背皮伤不说,后面驶来一辆汽车,贴着倒地的国辉头皮几厘米远,呼啦碾过去......
所有周围骑手吓得脸变色。贫下中农急停车。一群年轻工人红紫脸围上去。要干架?没有,愣头青贫下中农也吓傻了,向工人阶级嗫嚅道歉,要送受伤的国辉去乡里卫生院。
惊吓只在半分钟,国辉已从地上骨碌爬起,拍拍满是灰尘的头发,将自行车扶起,车龙头扳正,再拍一下愣头青贫下中农的头,“记牢,工人和贫下中农是兄弟。以后要兄弟帮兄弟。懂了伐?”遂翻身上车,又手搭上另一台拖拉机。所有人,风一般跟上。
这故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沪闵路上,在我们骄傲的小青工嘴里,成为“传说”。
骑行在沪闵路上的女工
穿过40多年光阴,依然记得沪闵路上徐闵线公交车的站牌点:徐家汇—漕宝路—西牌楼—梅陇—莘光小学—莘庄—春申桥—徐家湾桥—颛桥—精神病医院—北桥—畜牧场—剑川路—招呼站—轴承厂—一号路—西渡终点站。西牌楼在今天铁路南站位置;而当年荒郊的莘庄,是此路的“南北分界线”;骑过外墙暗红色的精神病医院,心想有没有女精神病人透过密密的铁窗在张望我们;过招呼站,是提醒骑车人,目的地将临,现代化工厂天地要到了。
今天的沪闵路
今天造访沪闵路,观望许多空调大巴车串起的徐闵线,细看新站牌,有删减,有替换,有新加。新加的路,都是金银满地喜气的名:报春路,银都路,金都路,贵都路,金塔路,鹤庆路。这些路的左右,万丈起高楼,想原来,这里都是稻谷满地香,桃李满天下。
历史留下了沪闵路,照单全收地保留了它的长短宽窄,但路两边,不见初始的景致。
忽然想起个人:杨妙贞。杨是沪闵路上的骑车女王。当年的一出《红色娘子军》受到我们尊崇,杨在工厂,也受到“娘子军”般尊崇。为什么?因为她和最强劲的男子一样,将沪闵路十几年征服在骑踏的脚下。甚至,许多男人也不能跟她比速度。
当年有句话:“苦不苦,想想妙贞的咸菜肉丝淡馒头。”此话怎讲?杨家住闸北西宝兴路上,10个平方米居10口人,大弟在部队因公牺牲,丈夫工作在遥远外地。家中她老大,60元的工资要承担三代人生活。她一月留给自己的生活费是多少?6元。杨骑行沪闵路的原因就两个字:节约。她极度珍惜那辆26英寸凤凰自行车,是厂里允许她分期付款而得到的,一月10元,12个月付清。她要让这辆自行车“生出钱”。
骑自行车,一个月省下来的公交车费用,近6块钱。
每周她在厂里吃的菜,是骑车从家里带来的一大瓶咸菜肉丝,就着食堂里的免费汤,顿顿吃得香,有人遂叫她:“咸菜肉丝”,她快乐应之,咸菜肉丝便成为她另一个名字。
厂里兄弟姐妹一起加班,加班的奖励是一张淡馒头的券。便有人说:杨家一帮兄弟胃口大,券省下来给她。杨妙贞啥东西都不要人家的,唯有这淡馒头券,她感激不尽地收下。到周末最后一餐,集中买进,骑车带回家,“沪闵路上我骑得飞快,一路风景越看越好看。想厂里兄弟姐妹一片情,家里人马上都能吃到白胖的淡馒头,开心唻。”
时至今日,我将当年有人说的话告诉85岁的杨妙贞:娶妻当娶杨妙贞。她竟黑色幽默了一下:“瞎讲有啥讲头,沪闵路听到也会笑出声。”
当年沪闵路上骑车女王杨妙珍,今年已经85岁了,精神矍铄
沪闵路上不会再有杨妙贞那样的人了。
他们是不可少的螺丝钉
王美珍说:“我一家,大半的人都在电机厂里打磨成器。”
上海电机厂一号正门就在当年闵行一号路(现在叫江川路)上,曾经的号码:一号路555号。她父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带着母亲,从川沙乡下出来,靠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走进电机厂的门,就此深深扎根,做冷作工,一做做到七级半工,当年评工资,105元,“自己也吓了一跳”———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父母育六个子女,王美珍老幺。前面几个,大哥当了兵,回来入了电机厂,二哥随即读书考进。还有一个小姐姐,最后顶替父亲,也一头扎进了这工厂,开大车间头顶上来来往往的大行车。
上海电机厂内的厂内铁轨
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普通人不会受很多诱惑,选择一个地方,认准有个好发展,铆着劲干活就是。老闵行,电机厂,大门口每天几万人汹涌吞吐,他们就是隐没在其中的几颗小螺丝钉。但螺丝钉有自己生存的意志、毅力和快乐。
家里发生这样一件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母亲的一场大病和在病痛面前的不屈抗争,且和沪闵路相关。
都说母亲活不长。但父亲对母亲说:“厂里管我,我要管好你。你心宽,就能活回来。不怕,我带你去看病。”那是怎样的坚持,除了工厂上班加班的日日辛劳,周末,父亲骑辆自行车,车架后面驮着母亲,风里雨里日头里,骑在沪闵路上,一次骑行几十公里,往莘庄,往上海(那时对从郊区到市区的说法),再一脚脚骑回老闵行,往返一次5个多小时。也算一次次“长征”。
母亲有退缩,几番打退堂鼓:为治病,买各种贵重药,原来收入宽裕的家庭难撑持。父亲说,我有力气,家里孩子等着你。“你看笔直直的沪闵路,一路没障碍,我们就要给孩子立榜样:不泄气。”
骑了整8年。终于,这病魔终被驱赶殆尽。一对恩爱夫妻扶持到老,母亲活了八十二,父亲寿享八十七。
王美珍讲的,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家的家风。父亲说自己缺文化,那就老老实实在厂里只干活少说话;母亲身体不好,那就负责养好身体顾好家。家里最早的房子,是工厂分配在一号路边十几平方米的屋,三代七口,睡觉全是双人铺,酷热寒冷共担。现在回想,兄弟姐妹的感情那时处得最浓。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改善住房,分到27.2平方米的居室,全家欢腾,感觉已生活在天堂。
王美珍说自己已是老闵行的“原住民”了:生于兹,长于兹,学习于兹,工作于兹。守着老闵行,守着已变成江川路的一号路,心平气和地生活。
我对王美珍说,40多年前,我们工作在工厂,骑行在沪闵路,生活在一号路,有赳赳之气。想到当年两句话:到了上海不到闵行,等于没到上海;到闵行不去看“四大金刚”(四个万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白走一趟。
王美珍笑起来,说现在她常去市中心,乘车过沪闵路,时常想:父亲早年用自行车骑着病弱的母亲,一脚一脚吃力伐?父亲母亲,这样的坚持和努力,想想,也很伟大。
沪闵路上唱歌的农家娃
严平和我们有十多年友情,却在近日,无意中说到一个共同话题:沪闵路。他说,我就是沪闵路边长大的农家娃。
我对他说:40多年前,在沪闵路上,我们工厂小青工,来回在市区、老闵行间骑自行车,和你父亲后座驮着年幼的你的自行车,或许哪一天,是交叉而过的。他说:很可能啊。
今年50多岁的严平讲起40多年前,他在沪闵路上看见那些“上海小青工”时的憧憬:他们经常穿着工厂的劳防服装,骑着自行车,也有乘在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厂车里。他一个乡下的小学生,羡慕嫉妒恨也来不及。他的出生地:颛桥乡友谊大队第六生产队,父亲则是中学教书匠。小学去莘庄读书,走路要两小时。走就走沪闵路,也乘徐闵线公交车。上了徐闵线,小孩时身子往下蹲一蹲,不到买票“身高线”,可以省下一角五分钱。后来人长高,那就多走一站路,少乘一站车,省下五分钱。走路时要走过那个精神病医院,害怕精神病人忽然冲出来,就唱当年的一首首歌,给自己壮胆:“打蛇打七寸,斩草要除根,批林批孔齐上阵,革命向前进”。也唱:“小松鼠,快长大,绿树叶,发新芽……”
上世纪七十年代沪闵路边的农家娃严平(右一),后面是他的父亲
以往,沪闵路上可以看到农民在三夏、三秋、双抢。有时我们工厂小青工也会在农忙时呼啦出动,帮贫下中农兄弟一把,和贫下中农“三结合”。但我只去过奉贤,靠近南桥。沪闵路上,对贫下中农劳作的身影只是遥望。
严平是看着沪闵路的变化长大起来的。记忆中的学校暑期,也要忙农活,到队里饲养场烧茶水,茶水里放决明子和大麦。烧了水,嘿呦嘿呦送田头。这劳动也算工分,一个工,三角三分钱,和大人一个工一块钱有区别。快乐的时光是随哥哥到河浜边抓蟛蜞,回来煮个蟛蜞烧老黄瓜。调皮的事情也发生过,到沪闵路旁边,偷吃别人家未熟的桃子、甜芦粟,挖人家的山芋,摘别人家的西瓜,被发现,被告状,然后,“吃一顿生活”。
那时候我们工厂中班下班,骑车回上海,晚上八点出老闵行厂门,回上海的家,要夜里十点多。一路沪闵路,除夜行的拖拉机突突驶过,黑灯瞎火,但闻声声狗吠。严平听了笑起来:那时的乡下头,尤其在夜里,给你三句话,通话靠喊,交通靠走,治安靠狗。
往事可回味:在沪闵路边一处水稻地里,严平曾举着一长棒,衔一长线,去吊水中的青蛙。有架轰隆隆的飞机头顶飞过。他便想:我这个“农家娃”,这辈子会乘上飞机吗?
而今,他这个研究生毕业好些年的国家干部,一次次去国外考察,再回到沪闵路边的家。
回味回不去的往昔。好在,巨变后的今日,也自有一味别样的芬芳———去看看香樟葳蕤的沪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