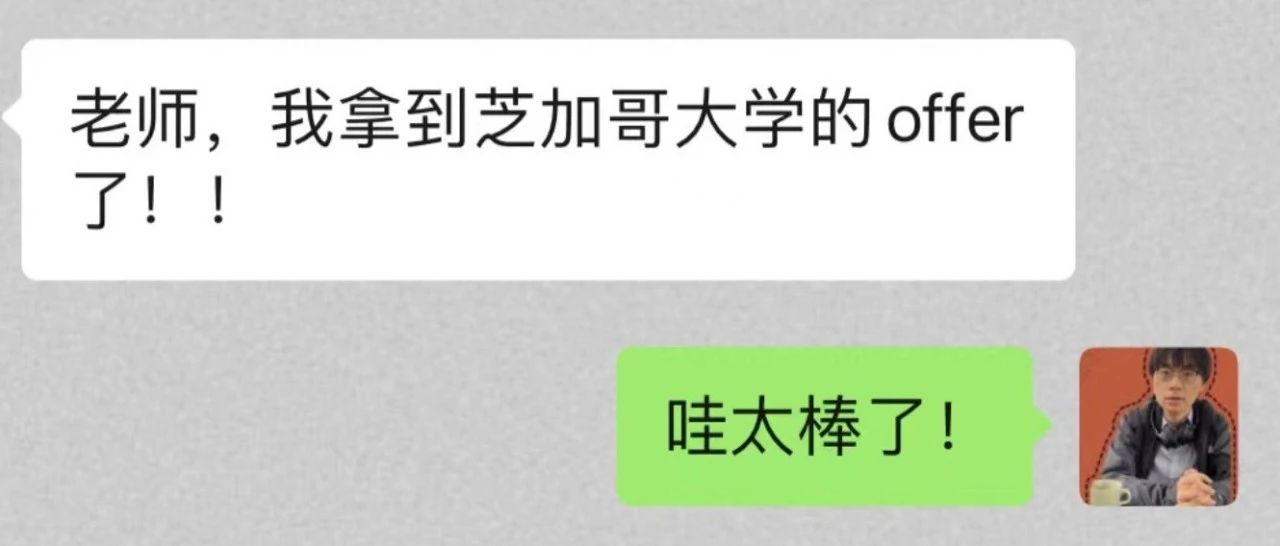清明又至。照例,倔老头朱远康拄着拐杖,带着香、纸、炮和一瓶二锅头上朱家山,去探望老兄弟朱马路,三十年来,这是他雷打不动要做的事情。
今年儿子再次劝阻这位50岁的老父亲:“您都这般岁数了,就由我替您上山去祭祀吧。”
“你懂什么,只要我这身子骨还能动弹得,就由不得你来,这是约定。”父亲的话语里是坚定,是不可质疑。
上山沿途的小路,罕有人迹,树和茅草卯着劲生长,山路两边荒草丛生。路不远,三十几年前,只不过朱远康一刻钟的脚力,只是岁月不饶人,如今又瘸了,半小时走不过山腰。
“老了,不管用了。”他在嘴边嘀咕,杵着喘粗气。在半山腰停下来,望向北方。回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18岁的他和同村21岁的朱马路,一起从军,远赴边疆,在黑龙江漠河驻扎,中国最北的边境。
在那个时代,当兵是一件稀疏平常又理所当然的事情。只要国家有需要,青年们凭着一腔热血,沸腾在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上。这是他俩第一出远门,坐绿皮火车,欣赏沿途的风景,火车在崇山峻岭之中蛇形穿梭,一路向北。越往北走,蔚蓝的天空越发辽阔,深褐色的大地上松针林此起彼伏。在火车上,他们俩比邻而坐,朱马路把话腔拉开:“不用怕,跟着哥走,怎么去我们就怎么回来。”
“嗯,当个军官回来,给老朱家长脸。”朱远康嘻嘻笑着说。
“小弟,不管最后我们谁能活着回去,记得给对方爸妈养老送终。”朱马路脸色凝重的说。
“丧气,你妈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朱马路沉默良久,没有接着话头继续说。
两天后,抵达黑龙江市,坐汽车直下漠河县,换牛车星夜赶往北极村。那里有一群人正在迎接他们的到来。
四月底的漠河县,白天怎么穿也不觉得冷,深夜却低至零下10℃,穿两条棉裤腿脚依旧直打哆嗦。坐在屋内时,恨不得躺在炕上取暖。北极村,在漠河县的最北边,比漠河还要冷。那里驻扎着一批队伍,北极哨兵。
北极村每年总要来一批新兵,今年四男一女,来了五个新兵。当晚连队开展迎新晚会。在村落的空地上架起篝火,刚屠宰的肥羊,挂在篝火中烤炙。小酒馆打回来的二锅头,五斤装,提两壶往回赶,一切正在筹备中。
今夜无眠,士兵们的军歌声嘹亮东北的上空。士兵们的舞蹈律动在这片黑土地上。大口吃肉,痛快饮酒,作为地道的南方小伙子,朱远康第一次感受到了北方的辽阔,北方人的豪爽。他爱上了这片土地,更爱上篝火晚会上跳舞的方红姑娘,她的舞姿锁在了朱远康脑海,嵌在他的心房。
第二天醒来时空地上灰烬,依稀使得朱远康,回忆起昨晚的晚会。连长告诉他,一早大家都奔赴各自的区域。新兵带训,以师徒制带训。每一个新兵,都会由一名老兵来带训,跟着老兵学巡防。
在同行人之中,朱远康最高,体魄最健硕,但年龄最小,所以连长留下他自己带。以后的生活中,时常能看到朱远康牵着马在前,连长骑着马在后,在国界线上巡防。这应该是朱远康最快乐的半年,虽然偶尔会思念起方红姑娘,偶尔也想见一见朱马路。
朱远康再见朱马路时,已经是一年后。接到命令后,朱远康奔赴到朱马路管辖的区域报到。抵达后才得知:朱马路在巡防时,遇山洪爆发,连人带马一起冲到河流最下游。找到人的时候,只剩下一具尸体躺在岸边的乱石上,马儿在河边吃着新鲜的嫩草。
此时看着躺在冰冷的棺木中的朱马路,脸色安详而苍白。他依稀记得,一年前出远门,母亲把自己的手搭在朱马路的手上说:“你年长一些,是哥哥,一定要带着我们家远康回家。”
朱马路走后,朱远康才意识到,在茫茫漠北大地上,唯一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抵抗无聊,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他接管了朱马路的战场,对这片大地上的每一条道路越来越熟悉,但是内心的陌生感却快要把他吞没在茫茫的漠北苍穹之下。
朱远康接过那匹瘦马,马的性子烈,认生,陌生人没个三俩下子绝对坐不上马背,即使坐上了也摔个狗吃屎。朱马路第一次骑它的时候,驯服了它,可惜这匹马再也跑不快了,右前腿瘸了。
三年里,朱远康在北境,每天在边界地段巡防,用他的血肉之躯作为边防的第一道防线。也守着一座新坟,里面埋着朱马路客死异乡的孤魂。
七月,漠河境内,依旧大雨滂沱。雨势稍降的时候,朱远康牵着那匹瘦马去河上游防汛。他注视着眼前这条浑浊的河流,河面比往昔更加开阔,河水波涛汹涌。朱远康连夜骑马返回村庄,通知全村做好防汛工作。接踵而至的洪水在深夜无情的席卷而来,那一晚,整个村庄受灾,幸运的是几乎没有人员伤亡。当时唯一的伤者朱远康,拖着右腿,一瘸一拐返回上游继续坚守。
朱远康回想起昨夜的惊险,依旧历历在目。往常通过村庄必须跨河,河水很浅,骑马很容易淌过河水。昨晚的河水淹没及肩,马儿刚走到水中间,突然暴躁起来,朱远康抵死勒住缰绳依旧被摔下马背。缰绳缠绕在手上脱不开,马上了岸以后,将朱远康拖行数十米的距离,摔断了右腿。
这是职责,他是这样认为。但是当职责和自己的生命产生冲突的时候,他回想起来依旧后怕,脑海中浮现出朱马路安详而苍白的脸。第一次产生了后悔的念头,他是真怕了。腿已经断了,命不能丢了,他和朱马路的约定还没有完成。朱远康心里想着,该去个申请复员。
是年十月,朱远康复员回家,全村子人在村头迎接英雄回来。却没有任何人知道,三个月前的那个夜晚他经历过多少挣扎。他之所以能回家,代价是当晚他自己动手彻底废了自己的右腿。
回家后,朱远康才得知,朱马路的母亲三年前已经过世了,政府出资在朱家山给朱母立了一座墓碑,还给朱马路起了一座衣冠冢。
回乡的第二天,朱远康拄着拐杖上山,跪在坟前,一瓶苦酒下肚,湿润的眼角挂不住的泪水往下落。这瓶酒一喝就是三十年,这上山的路一走就是三十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