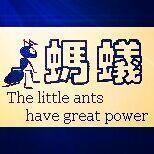楚武王熊通称王之后,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征战和扩张。周桓王十七年(楚武王三十八年,鲁桓公九年,前703年),败邓;周桓王十九年(楚武王四十年,鲁桓公十一年,前701年),也就是春秋小霸郑庄公死去的那一年,败郧(yún);同年,与贰国和轸(zhěn)国结盟;周桓王二十年(楚武王四十一年,鲁桓公十二年,前700年),大败绞国,“为城下之盟而还”。
一连串的胜利让楚国上下普遍产生了轻敌思想。周桓王二十一年(楚武王四十二年,鲁桓公十三年,前699年),楚武王派屈瑕率军讨伐罗国。令尹斗伯比在送楚军出征的时候,看到楚军“举趾高,心不固”,断定必然会失败,于是劝楚武王赶紧增派援军。
可是楚武王没听,不仅没听,还把这件事当个笑话学给自己的夫人邓曼听。邓曼这个女人很有见识,她劝楚武王说:“斗伯比不是仅仅劝您增派援军,而是告诉您主帅屈瑕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必然会小瞧罗国。您如果不及时戒饬,楚军会因为放松警惕不加防备而导致兵败。”楚武王这才恍然大悟,急忙派人去追,但已经晚了,没有追上。
果然,楚军军纪松弛,轻敌冒进,在罗军和卢戎军的夹击之下大败。打了败仗的主帅屈瑕畏罪上吊自杀,败退回来的其他将领则都按规矩被关了起来听候发落。楚武王认为是自己没能及时戒饬大家不要骄傲轻敌,所以这次战败是他的罪过,于是下令把这些将领都赦免了,表现出作为一名政治家的过人之处。
此后,楚武王没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样一直过了九年,到了周庄王七年(楚武王五十一年,鲁庄公四年,前690年),也不知道登基已经有七年之久的周庄王是哪根弦搭错了,在楚武王称王过去了十四年之后,突然又想起了楚国称王这件事,把随侯召去责备了一番。不知道随侯跟周庄王说了什么,楚武王听说后,偏说随国要背叛自己,于当年三月第三次率军攻打随国。明明是楚国自立为王,随国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想来也真够倒霉的。
这次伐随是楚武王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战。在出征前斋戒的时候,他就感到心里慌乱不安,今天看来大概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结果还没等大军到达随国,他就死在了军中。楚军秘不发丧,继续进军到随都城下。大概是上一次大败的阴影还没散去,随国这次一改狂妄轻率的虎样子,变成了卑躬屈膝的怂样子,连动都没敢动一下就直接请求讲和了。
这正是楚军想要的结果,于是他们以楚武王的名号跟随国缔盟而去,渡过汉水后才宣布楚武王已死的消息。我们不知道随国君臣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怎么想,不过,楚军敢秘不发丧,坚持达成战争目的再撤军,说明这个时候的楚国的确是个富有朝气的国家,正处在上升期。这样的国家,在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之后成为雄踞南方的大国,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楚武王一生无数的征战中,有一个连发生在哪一年都不知道的事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的攻克权国事件。《左传》记载这件事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这就是说,楚武王给权国派了个“尹”去管理它,而没按老规矩给它封一个“君”,虽然史书中并没明确说这个“尹”就是后来的“县尹”,但不管这个行政单位叫县还是不叫县,它都不同于以往的“国”或“邦”,所以人们一般乐于认为这是国史中置县的开始。
由于“废分封、行郡县”是国史中顶大的一件大事,因此县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是一个很吸引人眼球的事。楚武王从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90年共在位51年,认为“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这件事发生在这半个世纪之内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认为县就是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的,那可就要犯错误了。
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免瑚”铭文中有“司郑還林眔(dà)虞眔牧”的内容。这里的“還”与
“寰
”通,都是从“睘”得声的,又由于“睘”与“县”古音均属匣母元部,声韵皆同,所以也可以用“县”字代替,也就是说,这里的“郑還”就是“郑县”的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县”的最早记载。它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县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这时候的县是指环绕在国(城邑)四周的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鄙”,还不是我们后来所理解的那种县,所以我们经常能在古籍中见到诸如《左传·昭公二十年》“县鄙之人,入从其政”这种县鄙连称的情形。
不过,虽然县和鄙在地理上是重合的,但却不见得它们在政治上也是同质的。首先,《周礼·地官·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这里的“县”是一种划分土地的单位,而“鄙”则是被划分的对象。其次,《周礼·地官·遂人》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zàn),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这里的“县”是一种居民组织单位,“鄙”是它的下级单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周礼·地官·遂人》又说:“遂大夫备掌其遂之政令……,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鄙师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酂长各掌其酂之政令……,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邻长掌相纠相爱……”,《周礼·秋官·县士》也说:“县士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而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这就是说,本来是居民组织的“县”和“鄙”同时也都是行政单位,“县”更是还成了司法单位。
很明显,“国”肯定要对它城外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管理,所以“县”和“鄙”自然也就难免变得具有行政职能。不管是天子还是诸侯或者是更小的封建主,他如果既不是亲自进行管理,也不是把他的土地和人口一点不剩的全部分封出去,那他就只能委派诸如县正、鄙师和县士这样的官员代行管理;同时,如果这个封建主的实力足够大,拥有好几个没被分封出去的城邑,每个城邑照例也都有自己的“县”,那他也就还需要在自己的管理中枢设置《周礼·地官·县师》所说的“县师”,以便对这些个县的人口、牲畜、田亩、收成以及车辇、旗鼓、盔甲、兵器等手工业品进行统计、计划和调拨,统一管理它们的生产和分配。
从“国”需要对它城外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管理却又不能把土地和人口完全分封出去的角度来说,“系于国”的县一定不会晚到周昭王时期才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它即使不是伴随着“国”一起出现的,也一定会是伴随着“国”的扩张而出现的。这是与《周礼》这部书的真伪无关的结论。
这就是说,所谓“县系于国”指的正是这种直辖式的组织形式。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古人才借用了本义表示悬挂的“县”字来代替“還”“寰”等字,并最终造成了久借不归、本字反倒湮没不闻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