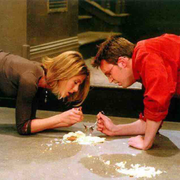前段时间因工作关系,看了项美丽的《潘先生》,邵洵美的《上海一年》,盛佩玉的自传以及一些邵洵美相关的论文、专著中涉及他的环节。
最后发现最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个人对同一时期彼此之间的表述。换句话说是他们眼中的彼此。这中间牵涉的视角包括男性与女性,美国与中国,美国现代女性与中国传统,妻子、丈夫与情人等等。你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误会与刻意的规避。
先说邵洵美,这些年已经有非常多的论文、专著讲述他,李欧梵《上海摩登》中,将其形容为颓废的摩登的唯美的。作为民国著名出版人,也已是定论,最初可能是一个贵族子弟的念想,后来变成一项事业。他的出版事业牵涉领域十分广,带着上海滩的光怪陆离的色彩。《金屋》杂志,注重装帧设计。《时代漫画》,为民国的漫画提供了重要的舞台。他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最兴旺的1934-1935年间,曾同时出版刊物多达七种。当然也因为内容良莠不齐,遭受诟病。他还曾经印刷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英文版单行本。
他注重印刷质量,斥资五万美元采购德国影写版印刷机,战争开始后,这套印刷机由项美丽从杨树浦帮其抢救回来。邹韬奋的《生活》、《万象》都曾由其时代印刷公司印刷。新中国成立后,这套印刷机由夏衍牵线,由政府收购,后印制《人民画报》。
邵洵美的朋友圈非常广,徐志摩、徐悲鸿、常玉、张道藩等等都与其有着相当深的友谊。他的妻子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嫁妆丰厚,她的家族支脉非常广。将这两个人的亲戚八一遍,基本就是半部文学史、美术史、政坛史。
项美丽是个勤奋多产的作者。她一生为《纽约客》撰写二百余篇文章,出版五十四本书。二战前关于中国的冒险文章最有影响力。当然她的写作领域非常广,非洲、作家劳伦斯、长臂猿、钻石,她均有涉猎。
项美丽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美国女性,她渴望冒险与挑战。她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矿业工程学位的女性,毕业后曾经在德库石油公司工作过一年,很快厌倦了这样的生活,1924年,她开启了作者生涯。受查尔斯·林德伯格横飞大西洋的感染,项美丽也想获得那种自由,1930年,她乘船前往非洲,在那里的红十字会医院工作,与当地部落Pygmies生活在一起。
看《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可以知道,二战给了女性很多工作的机会,但是战后女性还是被倾向于认为应该在家庭中。所以项美丽在那个年代依然是很前卫的。
1935年,《纽约客》聘请她为中国的海外通讯员。起初她并没打算在上海居住五年,她想的是来看看,写些文章,然后可能再回非洲。她决定留在中国不走的原因,除了邵洵美带给她的丰富“专栏素材”,可能还有上海的优渥生活。
她在《中国与我》中曾经写道:我常常为自己的花销惊叹不已。战时物价取决于米价,但在我们看来,米价便宜得跟不要钱一样。中国人的购买力和我们有很大不同。对我们而言,便宜的米价意味着廉价劳动力,这又意味着廉价商品:家具、仆人、服装、蔬菜,就这样我坐在了金字塔顶端。我不负债,我衣食无忧。
以此来看,不论哪个年代,女性的自由必须依靠经济自由。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稿费比较高这一点在邵洵美《上海一年》中也得到侧面证实。战时(1937年)邵洵美财务紧张,当时项美丽邀请邵洵美与她合作文章,各得半数。“第一个星期里,我们合作了两篇文章,由航空寄到美国;果然回信里附来一张支票,数目大得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假使每篇文章都能如此,还愁什么吃着?”
能让邵洵美惊讶,且又能让觉得他养活一大家子人不愁吃着的稿费数目应该是非常高了。不过很快,随着战局的形式改变,外国读者眼光也变了。“和以前同样性质的文章已不受人欢迎,我的收入便又没有了着落。”虽然项美丽坚持要预付邵洵美稿费,但他自言不敢接受她的好意。
那些文章中,有不少便是《潘先生》。当然二人合作巅峰并非此,邵洵美牵线,掩护杨刚翻译的毛泽东《论持久战》,项美丽也参与其中。项美丽能够采访“宋氏三姐妹”,邵洵美出力不少,宋蔼龄早些年曾经做过盛五小姐的英文教师,盛五小姐是邵洵美的姨母,盛佩玉的姑母,盛七小姐盛爱颐则与宋子文有过一段爱情故事。
回到《潘先生》,这组文章最初是项美丽作为《纽约客》的海外通信员写给美国读者的。潘先生的原型就是邵洵美,因此他的妻子、父母兄弟那一大家子的麻烦与生活都被装进文章中。文章中掺杂的是一个美国女记者的视角,纪实成分居多,同样也带着一点虚构。
在这些短篇文章里,潘先生有时候是面目模糊的,悠哉悠哉地出现,你很难判断他的行为动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贵地提供了一个美国冒险女性的她者视角。她是战时上海生活的闯入者,又是参与者(《杨树浦》一篇中,她利用美国身份帮助邵洵美抢救回德国印刷机),她十分好奇地观察记录下这一切,基本不做评判。
邵洵美,在1938年10月,写就的《上海一年》大概几万字,以他的角度回溯了他的心路历程。《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则是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晚年自传,历尽沧桑后,她回望当年的上海生活。
也就是这三个文本中,项美丽是文学性的,邵洵美偏纪实性,盛佩玉的自传则掺杂了时间,非当时即战争时的记述。
《潘先生》中《首饰盒》讲的是盛佩玉。项美丽写自己对佩玉怀有祖母说的恻隐之心。“因为我是个对妇女权利有先见之明的年轻美国女性。我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妇女正身受压迫。事实证明我很正确,佩玉正是我想找的对象。”在项美丽的描述中,盛佩玉个子矮小,很漂亮,对自己的美丽却一无所知。喜欢时尚,胆小善良。
最暴击的是对盛佩玉一个人过马路而自豪的描述。“她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过马路,从来没有,所以她觉得自豪。”这是文章中,潘先生转述给项美丽的。项美丽的反应是晴空霹雳,站在那抑制自己,以免哭出声来。接下来的话仍然是潘先生的转述,佩玉想让项美丽搬去住一起,“最好让你的朋友看到你和一家人一块儿生活,有人照顾你。她总是担心有人半夜去拜访你,或图谋不轨”。“你一个人住,又没有结婚,我妻子很担心。”
这对单枪匹马闯荡非洲,又在异国他乡居住生活的项美丽来说,那句“一个人住,又没有结婚,很担心”这种类似的话简直太不可思议。对今日女性已经拥有极大自由的我们来说,重新看,可能也会觉得:盛佩玉真的是过于担心了。而且太大小姐,连一个人过马路都要感到自豪。
再看邵洵美《上海一年》,开头邵洵美便说自己无时无刻不被俗累枷锁着。唯一感到安慰的便是妻子的信心与同情。
最后一次,老婆把我们几个女儿的小首饰裹在一个小手巾包里对我说:“以后恐怕没有再配进娘舅家的东西了。”
这样的细节被邵洵美单独拎了出来放在这里。
1937年,邵洵美三次搬家,《潘先生》中也曾有记述,从杨树浦搬出来,因为战争,没得法,第二次搬家是为了有个安静的环境写作,第三次则是稿子的出路发生问题,紧缩开支。佣人、妹妹、自家儿女一大家人挤在小洋房中。邵洵美与妻子只能睡在楼下的饭厅。“我们在正中挂了个幕帷,靠外面的一半便做了饭厅和会客室。”邵洵美慨叹自己将没有机会再做什么文静的工作了,搬进去五天,盛佩玉“又照例”为他想出了个补救的方法。
原来推开楼下房间的长窗,外面有一个阳台,装上窗子很像是个小书室,八九尺长四五尺宽,足够放一张书桌,两只书架,几只小凳子,用了厚一些的幕帷,坐在里面,精神居然能集中。
盛佩玉将这里布置好,邵洵美立刻把自己关里面,为《天下》写的那篇《孔子论诗》就是在这个时候脱稿的。
盛佩玉对自己的美是有认知的,她在自传《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里写过自己的眼睛很美。她在写别人时也会不自由住说下那人的相貌,包括项美丽。“身材高高的,短黑色的卷头发,面孔五官都好,但不是蓝眼睛。静静的,不大声说话。她不瘦不胖,在曲线美上差一些,就是臀部庞大。”
她羡慕项美丽能写文章独立生活,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然后回去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
自传中有两个细节值得单拎出来。都是战时的事情。上海“灯光管制”,每个人家都要用黑布做窗帘,黑布灯罩里不露一丝亮光。有一天夜里孩子生病,保姆不小心牵动窗帘,露出一线亮光,不过一两秒的时间,巡查的日本人进园来打门,拳打脚踢敲打里面门,嘴里还骂人。邵洵美说去开门,盛佩玉说“还是我女人家去好。”便急忙下楼打开门。
日本人气冲冲地用中国话斥责一顿。我忍气吞声地告诉他,孩子生病了,照顾她不小心露了光,向他赔罪。他又大大地训了我一番,然后大摇大摆走了。
还有一个是她在马路上走。天空响起了飞机声,声音极快地过来了,她急忙避到身边的商店里。听到飞机声过去,便又出来再往前走,可飞机倒又在头顶上,惊得街上来往的人窜来窜去。
项美丽一定没想到,那个她笔下一个人过马路都要自豪的大家闺秀,战时一个人走在头顶上随时丢下炸弹的马路上。那个大家闺秀,在那样的情况下,还不忘避到一个有饭吃的店。“见有个沙利文西餐馆,我奔跑过去。点菜、等菜、吃菜,这段时间飞机过去了总算没有再来。”
将这些单独拎出来,是想说写作的陷阱与美妙。如果沉迷一个人的表述,会很容易陷入偏见。幸运的是,项美丽、邵洵美、盛佩玉都留下各自想讲述的东西。但是是否拼凑在一起就是真相呢?可能也非如此。
毛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过项美丽、邵洵美关系的不同表述:
西方人著写的项美丽传记《没人说别去》中,邵洵美是以一个“女性立场”出现的,他的美丽被人渴望观察,如同今天的小鲜肉。“男主人公成了一个被观看者,一个被西方女性所欲望的美人,邵洵美很像传统故事中,被男人垂青的女性”。
同样中国人写的传记、网络上流传邵洵美爱情传奇中,大家试图突出强调男人邵洵美用自己的才华征服了白人女主人公。“在他们的爱情中,作者渲染了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也暗示了项美丽妾的地位。”
如同今天放置在此间的节选。
邵洵美《上海一年》中的盛佩玉常让我想起冒辟疆写的《祭老妻苏孺人文》,与他写董小宛完全是两种笔法,前者是庸常的漫长岁月,后者则是浪漫的、文学式样的,连经受的苦难样式,二者都不同。如果苏孺人、董小宛分别来回忆自己这一生,有机会记述一生,会出来怎样的文字?
当然这里面又涉及每个人的文字掌控能力。显然盛佩玉是最弱的,她一直在那絮絮叨叨,掺杂着零碎的吴语,在今天也不够洋气。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她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