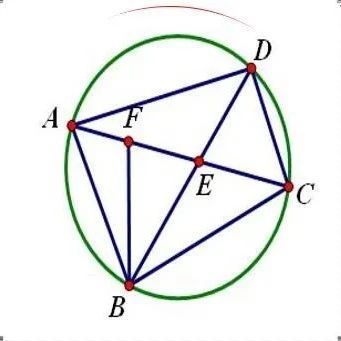(北方故居的门前摄05.6)
我有一个“宝物”,它是一只拳头大的珑玲小碗,白地银边,碗是纸质的,和普通瓷碗的厚度一样,银边是烟盒锡箔纸剪成的花边,碗身贴着鲜红的剪纸,很随意剪成的图形,有着半坡村人面鱼纹的朴拙味道。我把它摆在书架显眼的地方。它很特别,来自一个被我叫做“爱情泥屋”的地方。
2002年冬末近年关时,我和三姨去八十里外的平原上的小村庄,拜访我从未见过的亲戚六姨。冬的平原仿佛墙角蹲坐的那位晒太阳的老人,戴着皮帽子,披着老皮袄,袖着双手打盹,眯着老眼,还发出轻轻的呼噜声。天高远,地寥阔,苍烟老树寒雀,稀稀落落的村庄,炊烟静静屯在空中又慢慢散去。路上格外清冷,三姨指给我看,哪个村庄是我外祖母的娘家,哪个村庄又是我外祖母的婆家,甚至还有我外祖母的外祖母的娘家村……她平静地叙述听来的老故事,这样的行程像在寻根。到六姨家已经傍晚了,村供销社的大围墙,毛主席万岁的红色标语痕迹还很清楚地留着。
我们顺着村人的指点,找到一间低矮简陋的土屋,在农村,这样的土屋通常是农家随意垒就放杂物的。屋里钻出一个高大老人,使我确认是人住的地方,他是我的六姨父,招呼我们进屋去。小屋子隔成两间,外间二平米大的杂物间,小口袋和盆盆罐罐放得很有序,留出一条窄窄的通道侧身进去,里面是五六平米大的小屋,一围小炕,一个灶台,剩下的空地刚容两个人转身,小炕上的人们挨着挤着,却有十几人,围着小炕桌又说又笑,又唱又闹,坐在正中间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的那位老太太,是我的六姨,她在玩牌。
因我们是远客,村人知趣地散了。
六姨亲热地拉我脱鞋上炕挨她坐下,嘘寒问暖。她七十多岁了,瘦小单薄,常抽烟的缘故,说话爱咳嗽,面相看上去比姨父显老,笑起来像朵干巴的老菊花。她和我们在炕上拉家常,姨父在灶上忙碌做晚饭。他熟练地烧火,呛油,把冻了的粉条在水里泡开,把豆芽摘了皮,把土豆切块,把面粉和好成团……六姨父的眉毛很浓很黑,和大名人林彪的眉毛一模一样,他高鼻大眼,虽老了,但皱纹不多,腰身不挺拔了,还很结实灵巧,忙碌得井然有序,不让我们插手,自己一样一样地把菜做好了端上小炕桌,吃过饭,又动手洗碗刷锅,我要帮忙,六姨说不用,一辈子了,家里这些事情都是六姨父干的,村里的白事红事也都是找他当大厨,说这话,六姨很平淡,像拉家常。
原来六姨一家有足够多的地,给三个儿子娶亲盖屋后,不愿和儿子们挤在大院里,便在附近搭了这间小泥屋,老两口搬出来住。
这在村庄中习以为常,老人干不动活了,会自觉寻觅一个小窝过完最后几年,尽量不给儿孙添麻烦。
六姨的小窝不冷清,晚饭后不断有人来找六姨玩牌,有年轻人也有老人,看有客人又一个个走了。六姨说,他们搬到这间小屋后,不需要照管儿孙了,农闲季节,家里每天都是一屋子人玩牌,要茶要水六姨父在一边张罗,他不会打牌,坐在一边看六姨打牌。六姨笑说,一辈子都是她玩,他看她玩。六姨爱热闹,人缘好,她爱聊天但不絮叨,总是那么一朵老菊花的表情,笑眯眯地让人舒服。六姨父笑眯眯地坐在她边上听我们说话,为我们烧水沏茶,茶是这里人常喝的砖茶,味道简单,很香。他身上穿着一件褪色的质地很好的军用绒内衣,说是当兵的孙子给的,这使高大的他看上去很整洁很“帅”。
屋子矮,站在炕上,我的身高都要碰到天花板。泥巴墙上挂了两个大镜框,是屋里唯一的装饰品,镜框里的照片有我去世多年的外祖父的,还有我小时候的,保存得好好的,连我自己都没有见过。六姨打开屋里惟一的小柜子,拿出几个好看的小碗,拿出一盘子瓜子,让我吃,把瓜子皮丢到小碗里。
我一看那小碗就爱不释手,六姨告诉我,这是自家做的,一年用过的碎纸头,裱窗户的或粘鞋底用剩的纸,不乱丢,攒到年底了,用水泡成纸浆,拍打挤压后糊成盘、碗、盆,罐各种形状,再用攒下来的烟盒包装纸剪了花样贴在四周。这一带的农家老人都会这种手艺,它们是家具的一部分,拿来盛放各种干燥的东西,经久不坏,非常耐用结实。
这晚要睡觉了,六姨父抱来几床干净被子,给我们打来洗脚水。这一夜我在暖烘烘的炕上睡得格外香甜,一点没有作客的感觉。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要叠自己的被子,六姨父摆摆手,脱鞋上来,眨眼间,大大小小的被子枕头收拾得端端正正的,让我惊讶。六姨笑说打他们俩结婚到现在,一辈子了,都是他叠被子,因为他“叠得好”。
说话间六姨父早早把饺子面和好,饺子馅拌好,和赶来看望我们的表兄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子。我没有觉得小屋拥挤,锅里的水汽暖着我,灶上的火暖着我,六姨老菊花样的笑容暖着我,六姨父宽厚的眼神暖着我,我坐在这里,安心地包着饺子……我的目光更多地落在这位姨父身上,从进门起,都是他在忙前忙后照料我们,而盘腿坐在炕上的六姨,舒坦地很像一个老了的“公主”。
两位老人坐在小泥屋的热炕头上,讲这一辈子经过的事,没有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就是春种秋收冬藏,就是生儿育女,就是柴米油盐。六姨说姨父是早年村中地主人家的少爷出身,念过私塾,出去做过生意,是生活“讲究”的人,见多识广,做事情样样都是村中最好的。娶了六姨后,他只让她在家里带孩子做针线,洗衣煮饭收拾家务都是姨父亲自动手,而外面农田里的活,姨父做的更是好,到现在这岁数还闲不住,农忙了轮流帮儿子忙地里的活儿。他对她,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他心疼她脚小,体弱,什么都舍不得让她做,什么都是他自己做,怕她累着,总让她歇着”。
这里的物质条件很差,吃的用的都指着地里的收成,没有多余的奢侈享受。但看着眼前这对老人,我竟然会在脑子里冒出一句《西厢记》的词:“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账,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原是张生对红娘说的,但换了是张生对莺莺讲,是不是更有意思?笑得花般灿烂的六姨,被六姨父一辈子细致体贴着,在这天寒地远的贫穷村庄里,依着泥土,依着草木,粗茶淡饭的,“叠被铺床”的,相依为命的,让我对这间泥屋和泥屋里的人有了羡慕,他们不“贫穷”,他们很“富有”,多少钱都买不来两个人真挚疼惜一辈子的感觉。
我们告别要走,六姨父手拎一只杀好的大公鸡,六姨拿出一包饼干往我包里塞,我知道,这是这简陋泥屋一整年里最珍贵的食物了。我不要,我只往背包里塞了六姨亲手糊的小碗,插了姨父亲手粘的五彩鸡毛大掸子,我说我就稀罕这两样城里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这让他们很高兴。他们在小小泥屋前依依不舍地目送我们离开。
鸡毛掸子我留在了三姨家,实在没法带上火车,我只带回了那只小纸碗,闲了无事,我敲敲这纸碗,欣赏它的美丽,它不紧不慢蓬蓬有声,仿佛那小泥屋里温暖的家常闲话一句一句在耳边回响—“茅檐低小,屋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一个女人,得一个男人真心的疼爱怜惜,便是身在茅檐泥屋,一生也可以足矣。
图片上的纸浆碗是百度来的,就是六姨给我的那种碗,装饰也很像。至今家里还保存着数个大大小小的纸浆碗、纸浆盆、纸浆罐子,是家里的三姨、老三姨做了送给我和妹妹的。
2007.1.28